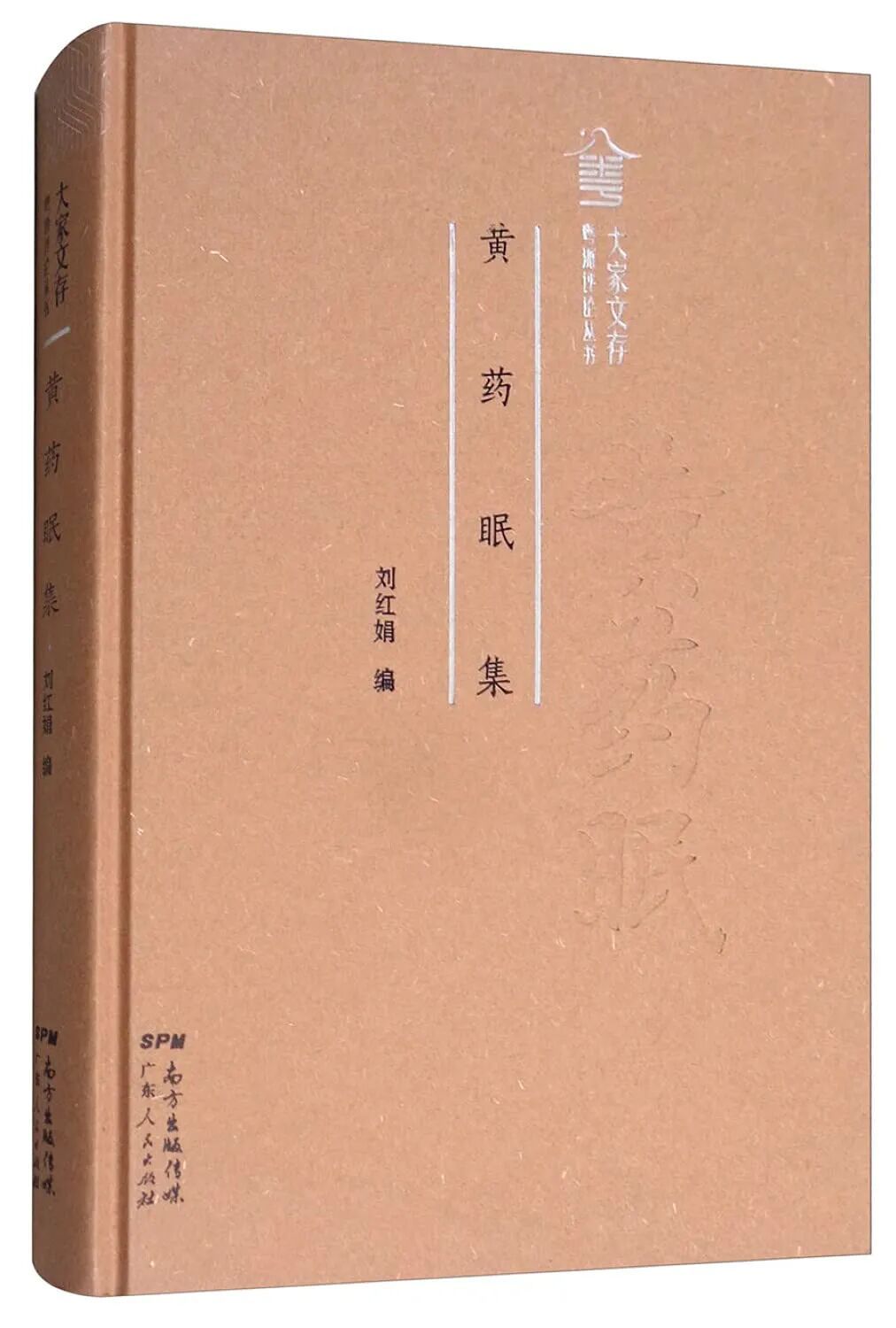
张可心
重庆大学中文系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5期
摘要: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黄药眠与生命哲学、共产主义于“十字街头”相遇,由此开启了富于创造力的文艺理论生产。以此为起点,厘清20世纪20年代创造社时期黄药眠的理论生成,对于理解其40年代“约瑟夫的外套”等问题别具意义。通过对法国柏格森哲学、日本大正生命主义、第二国际有机历史构成理论的透视可以发现:“生命”问题不仅与黄药眠的文艺理论紧密相连,甚至构成其迈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推动力。黄药眠的文艺构想与生物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话语并存、矛盾、对话,显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结构之间的错置。同时,黄药眠的文艺理论建构本身即是一种革命文化实践,其理论斗争呈现为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始终贯穿再“生”与变“革”意识。
关键词:黄药眠;文艺理论;生命哲学;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生成
引论:生命哲学遗产作为革命问题
1946年年初,黄药眠从梧州出发,准备沿水路返回阔别近二十年的广州。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他终于得以从辗转多年的西南大后方回到广东。当轮船重新停靠在粤桂交界处的肇庆时,眼前的风物让他想起遥远的大学时光:
离这里不远的郊外,有个顶湖山,山里有个寺,那里有美好的瀑布,瀑布底下还有个幽静的湖。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同学们一起到这里旅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见的大瀑布。当我看见细细的水珠以各种形式跳跃着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当时喜爱的哲学家柏格森的《形而上学序论》,他讲到人的自由意志就像这瀑布里面的水花向空中飞溅。这瀑布曾引起了我的哲学的玄思。现在想来,这种思想是荒谬的。但这些是我思想历程中的一个阶段,因此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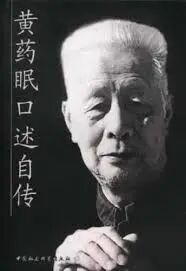
这段回忆出自《黄药眠口述自传》,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存在看似只是一条怀旧的脚注。但实际上,这个反复强调生命力冲动(Élan vital)2、生机、直觉、感觉的哲学家对黄药眠的启发不止于此。此处浪漫地理学式的“闲笔”并非黄药眠第一次提及柏格森和他的生命哲学。在这本自传中,黄药眠还详细回忆了柏格森《论生命力的冲动》如何为自己带来“像大瀑布冲刷之下的新花,晶莹焕发,腾泻周遭”的体验。3在多年后论及五四文学的知识谱系时,黄药眠不仅认为自己当时崇拜的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文学理论“导源于柏格森”4,甚至还将马克思的《资本论》、泰纳(Hippolyte Taine)的《艺术哲学》与柏格森的《形而上学序论》并置在一起看待,认为“从前读过大学的,都受柏格森影响”。5由此可见,黄药眠也曾一度感染T.S.艾略特所说的“柏格森主义流行病”6。
有趣的是,在黄药眠的论述中,柏格森总是呈现出一种“钟摆运动”状态。20世纪20年代时,黄药眠曾将生命力冲动论视为一种“腾跃晶莹”的形而上学思辨和诗学经验。然而,发表于1945年的《论约瑟夫的外套》一文却转而使用“破铜烂铁”7来形容生命哲学。这篇文章系统地驳斥了“生之冲动”概念以及相关的唯生史观,进而对胡风和舒芜的“主观论”火力全开展开批评。为50年代“美学大讨论”投石问路的《论食利者的美学》一文则将柏格森哲学视作五四运动中张东荪等“资产阶级”舶来的“进步思想”。8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几十年间黄药眠的摇摆态度?生命哲学只是被扫进垃圾桶的剩余物吗?还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更具体地说,黄药眠作为一个情感充沛的浪漫主义诗人如何在“理论战”中重审这份生命遗产?更宏观地看,生生不息的有机宇宙如何塑造了革命青年对文艺的想象,又如何“伴随着千万人的翻身”9结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世纪末意象?
近几十年来,得益于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人对柏格森哲学的重写及对情动转向(Affective Turn)的召唤,欧战后风靡一时的生命哲学受到了新的关注。然而,在中国本土领域涌现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政治光谱偏保守的角色身上,10是以生命哲学常被纳入“传统复活的主义之路”11中被考量;至于其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则常被忽略。学者张历君针对瞿秋白展开的思想史研究在此方面是具有启发性的。他提出了一种重要的发现,即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思想轨迹正好构成了瞿秋白靠向“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动力。12
本文认为,作为一个“战斗者的诗人”,黄药眠是另一种重要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政治案例。在他富于创造性的理论生产中,“柏格森”与“马克思”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长久以来,很多文学研究仅将青年黄药眠视作“创造社的小伙计”,从而忽略了其早期理论批评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重要性。顺着这一思路,本文希望围绕“四·一二”这一灾难性事变后的黄药眠,挖掘其有机的理论生成过程。不应忽视的是,黄药眠创造社时期的小说书写、在《洪水》和《流沙》上发表的文艺理论,甚至抗战时期的理论论战中都携带着生命哲学的“思想钢印”。同时,他又以演化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唯物论增补重写了“生命冲动”等概念。这种有意识的重写语言行动和历史批判姿态,正呼应着创造社左转时的自我认知思路:“奥伏赫变”(Aufheben)。
在创造社理论刊物《文化批判》的“新辞源”栏目中,这个词被介绍作德语“Aufheben”的音译词,用以形容辩证法的进程。在此语境中,“奥伏赫变”指在理论斗争的历史焦虑中有意识地丢弃、蓄积、扬弃。13在过去十几年针对“革命文学”论争话语的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音译词所暗示的复杂生成过程。一方面,它意味着有意识地从事一种关于社会文化的“全部批判”。例如,王璞的研究指出,“奥伏赫变”这个近乎“突兀的语言符码”是一种诞生于大革命挫败后的应激话语。它是一种象征综合重审历史体验的辩证意象,无论是郭沫若、后期创造社成员如彭康、李初梨,还是鲁迅,都身涉这一混杂时刻。另一方面,它又充斥着革命主体内部自我意识突变的焦虑。14例如,刘祎家的论文就刻画了革命主体改造自我而终于“紧紧内嵌于时代精神”的“过程性的‘成长’、演化状态”。15沿着这些思路,本文力图发现黄药眠在“四·一二”后的理论生成过程,探索他在“生”与“革”之间、生命哲学和革命意识之间的转换取舍、周旋复沓。
黄药眠的经验关联着彼时相当复杂的跨文、跨国、跨时的知识谱系。除影响力最大的柏格森主义之外,还有其在日本触发的“大正生命主义”(Taishō Vitalism)。16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还受第二国际文艺理论家们的“有机历史构成”论调影响。这意味着从方法上,我们需在细致的修辞、翻译层面重审“生”这一话语如何催生了黄药眠的历史阐释和文艺想象。
01
“梦的创造”:创造社、柏格森与厨川白村
1927年,黄药眠在创造社的《洪水》半月刊发表《梦的创造》一文。这一年,在潮州金山中学教书的黄药眠被卷入“四·一二”事变的漩涡,逃往老家梅县,随后又经王独清介绍来到上海正式加入创造社。而历经核心领导者郭沫若被通缉、郁达夫脱社等一系列低潮的创造社也进入了“洪水”时代的最后一年。从文学史的后见之明看来,他们正在酝酿次年全面转向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文学。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把1927年的历史镜头调整至广角,就会发现刚刚踏入昭和时代的日本也笼罩在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阴霾中。是年,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发表《二七年纲领》,将福本和夫运动定义为工人运动的分裂活动;同时日本官宪大量检举、抓捕活动家,共产运动濒临彻底破产的命运。铃木贞美在他的“生命观”研究中指出,正是这样的危机导致日本左翼知识分子为谋求活路而大力宣扬“社会主义”言论,“为此,礼赞‘生命’的思潮趋于衰微”17。这里所说的思潮,就是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的“大正生命主义”。这种思潮以柏格森学说为法国源流,以叔本华、尼采、豪普特曼等人的“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为部分德国源流。这些理论有着松散的论述外貌,如“生机论”“人生观”“生命主义”,等等。不过无论如何,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都以“人之生物生命为根本”,是“一种支配现代思想的基调,此基调存在一种重视生命之创造活动的倾向”,总体上属于一种“尊重精神文化价值的‘文化主义’”。18
铃木贞美的论述勾勒出一幅“此消彼长”的画面:大正生命思潮的消退伴随着福本主义运动和左翼宣传言论的高涨。无产阶级革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对抗性话语推动了昭和初期知识转型,这竟然导致日俄战争后蔚然成风的生命哲学直接走向衰竭。这让我们不禁感到好奇——创造社的情况又如何呢?根据伊藤虎丸的观察,创造社前期的文学青年深受大正文化主义影响,从而以浪漫派的艺术面貌异军突起;后期同人又受福本主义等理论辐射,暗合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左转方向。19那么,此时的他们是否也面临着一场“生命”与“革命”之间的“奥伏赫变”?从这样的历史情境来说,《梦的创造》可被视作生命哲学来到“十字街头”时刻的象征性书写,它融合了一系列矛盾的特质。远在巴黎的柏格森凭借《创造进化论》(L’évolution créatrice)斩获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本人不知道的是,此时自己的玄思正在风起云涌的东亚“旅行”,并被挑战甚至重写。
第一眼看上去,《梦的创造》是令人困惑的。与其说它是一篇成熟的理论文章,不如说它是一篇生命哲学、诗歌语言与社会理论拼贴而成的“蒙太奇”:文章开篇谈论生命的空虚本质,中间描绘诗人造梦而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悲剧,结尾处又论及马克思与共产社会——其核心主题很难一言以蔽之;再加之其典型的“洪水”美学风格,20过剩的感伤主义几乎快要淹没其批评主旨。但是,这种知识驳杂性正显现出黄药眠在成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前夜对生命哲学复杂的“转译”过程。
我们不妨先从对“创造”一词的基本语源学分析入手。不难发现,无论是《梦的创造》,创造社,还是《创造进化论》,似乎都无法逃避这个词汇的“诅咒”。而一系列考证可以证明,这是一种跨语际的谱系遗传。
首先,黄药眠所想象的“创造”是一种“生命创造”活动:《梦的创造》第一节就叫作“生之创造”。作者在此节发出抒情词格的呼号:“沉醉不醒的东方人哟,起来罢,生存是没有意思的,惟有能创造出生活的趣味来,生存才有意思!”21而这里所说的“创造”,建立在生命的“无目的论”上:
“生”不过是无声无臭的东西。“生”不过是由这边的死海跳到那边的死海的行程。所以它是没有“色彩的”,没有“目的”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类是绝对不甘寂寞的!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跳跃着,生出一种“生之欢喜”来!我们要奏出生之音乐来消除这个寂寞,要鼓动我们的情热去塞住这个空虚,更要把这个生命涂成了鲜红的色彩,要把这个生之进程移向一个空悬的目标!22
这段对“生”的诗意论述显然与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构成对话关系。在最明显的文本语言层面,“生之……”的修辞“公式”带有张东荪译版《创化论》(1918)的印记。在张译版中,章节名被译作“生之进化”“生之本义”等,全书的核心概念“Élan vital”(英译“vital impetus”)也被译为“生之冲动”。黄药眠的“生之创造”“生之进程”“生之音乐”等表述可以溯源至此翻译范式。23不仅如此,对“目的论”(teleology)的驳斥24同样奠定了《创造进化论》首章的理论基础。柏格森从组织学、胚胎学和博物学中得到启发,发现流行的哲学-科学“目的论”并不能解释生命进化的历史。他认为,生命世界并不能被人为赋予某种给定目的,也不能由特定机械方法加以计算,因为进化的动力是一种无限创造的生力冲动,它让这个世界无时不处于绵延、运动和变化中,而生命意识随之肆意流动。由此可见,黄药眠有关人类创造的想象诞生于一个动态的有机宇宙中,它脱胎自生物冲动。
不过,黄药眠的“创造”并不止于一种生命经验,它更是一种厨川白村意义上的“文艺创造”:“社会的梦幻者”等章节描述了一种诗人的创作活动。黄药眠认为,这种文艺创造的动机源自“苦闷”。文章中俯拾皆是的“苦闷”“人间”“情热”“欲求”“生之欢喜”等语汇构成了一系列连贯的厨川白村式生命主义修辞。显然,它们从“人间苦与文艺”“创造生活的欲求”“自己发见的欢喜”等《苦闷的象征》章节移植而来。25正如金德勒(Benjamin Kindler)指出的,厨川白村是连接“世纪末”(Fin de siècle)理论与创造社的一道中介。26鲁迅曾精准地道出其19世纪末理论资源:“作者据伯格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出生命力的根㭽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27黄药眠对于文学创造内在欲力的诠释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柏格森主义与精神分析科学的知识谱系对其兼有影响。
值得强调的是,此跨文化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创造”的语义转换:柏格森哲学中的“生命创造”被厨川白村确认为一种“精神生活的创造”28。更具体地说,黄药眠对“创造”的文艺转译集中发生在对“梦”这一暧昧意象的改写上。黄药眠将诗人视为“‘不满足’和‘缺陷’的本体”,而因这种“由缺陷求圆满的欲望”引起的书写机制被黄药眠比喻为一种类似“发梦”的表写过程。正如文章标题所暗示,这是一种“梦的创造”。黄药眠把“梦”视为文学书写机制的一种结构隐喻,这显然受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影响。心理分析学正是依赖语言文字对“梦”的阐释-翻译才得以整合人的意识,而这也正是《苦闷的象征》“白日的梦”一节的主旨:“将文艺创作的心境,解释作一种的梦”29。于是,柏格森的“生之意识”与文学书写联系在了一起。这意味着,经过一系列创作论、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的力比多外科手术,生命的内在经验(“心或精神的律动”30)外化为一种诗人的文艺生产,一种语言象征。
现在,让我们回到最关心的问题:这些生命-文艺“创造”,如何进一步介入了革命世界?黄药眠为“创造”增补了最具左翼文化政治内核的一笔:一种革命性的“历史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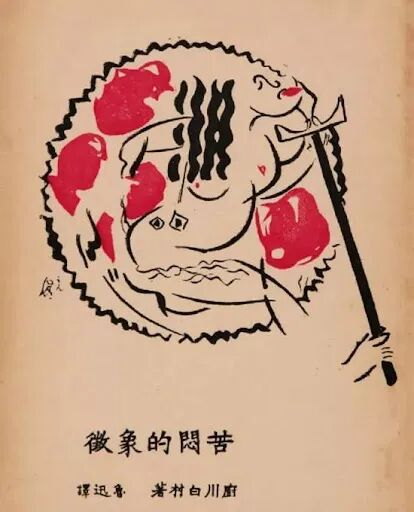
《苦闷的象征》描述了一种生命的“破坏力”形态:“生命的力者,就像在机关车上的锅炉里,有着猛烈的爆发性,危险性,破坏性,突进性的蒸汽力似的东西。”31这种力量是一种“突进和跳跃”32。厨川白村的“蒸汽力”意象显然也源自一个典型的柏格森式譬喻——《创化论》将生命冲动比喻作蒸汽机里的蒸汽喷发,向上喷发水珠形成有机生命,向下跌落则形成无机物质,二者势不两立,互相掣制。这种生命张力在黄药眠这里也埋下一颗与肉身捆绑的语言炸弹。《梦的创造》不仅暗讽“四·一二”的现实“权威却不能禁止人们发梦”33,而且以“跳跃”“鼓动”等文学修辞作为一种政治抵抗。
王璞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创造”一词的革命性内涵。他指出,当郭沫若将《浮士德》中“地灵”所吟唱的“geschäftiger Geist”一词翻译为“创造精神”(creative spirit)时,歌德所使用的原始德语概念指向了一种忙碌、能动、艰难、繁杂的活动。“创造”天然地携带着地灵形象的毁灭性能量,由是催生了一种时代精神下的革命行动主义(revolutionary activism)。34伊藤虎丸也注意到,从郭沫若的《创造》发刊词到周全平为《洪水》发刊所作的《撒旦的工程》,都可见从一而终的“破坏性创造”;他将其解读为大正文化主义所萌发的“艺术家意识”,只不过在后期创造社中,这种文化主义转变为“批判的精神”。35类似地,我们也可以将“梦的创造”读作对大革命失败境遇的批判性回应,它同时也是一种左翼政治的言语行动。在文章中,黄药眠不仅承认创造需要生物基础和艺术能力,更将“创造”视作“革命”的同义词。
在文章结尾“蜃楼”一节,黄药眠这样论述:
Hudson在文字研究导言里说“我们在知道之先,必然先觉到他”……故从这样说来,诗人实是历史的先觉者……谁敢说实践论的马克思没有受先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暗示?谁敢说马克思所预想的共产社会不多少含有他自己个人的幻想?事实的发生总在理论之前,而理论又必须超越现代……”36
黄药眠的历史创造不仅与文艺创作形成同构关系,甚至历史言说也深受文艺的指引,二者如铰链相缠。在他的构想中,“诗人”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身份是同质的,他们都是历史的先觉者。“诗”与“理论”也类似,它们都是试图超越“现代”的语言-预言。将空想放置在实践之前,将个体幻想放置在共产社会之前——乍看上去,这是对“正统”历史唯物论的颠倒,仿佛梦境与现实的倒错。但恰是这种“从无而有”的创造暴露了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语言焦虑,以及相应文化的早产。
柄谷行人在《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揭示了一种看似有违常识的历史言说的生成过程。他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是从‘肉体组织’所感知的缺乏和无力性出发,并且从那里发现了表象、欲望及语言的生成”37。也就是说,历史言说因肉体的“无力”和“匮乏”而发生。“梦的创造”也呈现出这种历史言说的颠倒。程凯的研究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意识革命与实际革命之间毕竟是一种不对等关系……大多数乘风而起的人并不真正了解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原理,只学得一些‘阶级意识’、‘无产文学’、‘方向转换’的名目”38。此时,黄药眠论及的“马克思”“共产社会”“实践论”还是一种未被全面激活的“潜意识”。在普罗列塔利亚文学转向正式发生之前,浪漫诗人的幻想既没有顺理成章地理论语言化,更未成为现实,因此当它出现在历史言说之“场”时,只能以错位的形式出现。当柏格森和厨川白村带着如梦似幻的创造动能接近中国的十字街头时,它不得不面对1927年残酷的历史境遇。
但也正是这年左翼意识斗争的疲软和低潮,才导致柏格森那种绵延不绝的生命创造力变得极具吸引力。“生之冲动”被黄药眠塑造为一种近乎先验直觉的动力,受此驱动,艺术创造也被构想为预言新世界诞生的历史言说。革命者被诗人带入一种浮士德神话:文学语言可以填充缺位的生命欲望。像伊格尔顿描述的那样,诗人作为“语言动物”永远面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危险”,然而文化语言对“现在”的不断否定和超越却使他们乐于冒险。39此时的黄药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梦”正在历史沸腾的坩埚中边滚动边寻索,并一步步进入布尔什维克有意识的革命道路。它被期待在理论语言的论战和干预中赢得“同路人”,或打败“孟什维克”们。
02
“生之可能”:演化生物学、文艺起源论与无产阶级革命
1928年,“生命”与“革命”的“奥伏赫变”还在继续。这一年黄药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大量阅读马恩著作,还通过英译本接触到苏联的普列汉诺夫(G.V.Plekhanov)、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等人的著作。40在1928年创刊的《流沙》上,他接连发表了两篇文艺理论,分别是《非个人主义的文学》(以下简称《非个人》)和《文艺家应该为谁而战?》(以下简称《文艺家》)。这两篇文章迅速理论化,一改苦闷的感伤诗人面貌而转向革命的战斗者姿态。用《流沙》的编后语说:“创造社的同人早已踏在时代的前头,严重的否定了一遍自己。”41此时他们开始认真研究“理论斗争”的可能性。
这一年黄药眠似乎已经习得了经典马克思的历史分期论和社会学分析,完美地契合创造社的普罗列塔利亚“急务”。《非个人》从“文艺起源论”入手,说明文艺本源自民众劳动,而个人主义文学是私有制度之“社会组织”的近世产物,因此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而言,新文学应该还“文艺”给“民众”。42《文艺家》则在社会制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工农阶级”和“革命”概念,说明文艺家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地位上表现出无产者的疾苦,提醒他们阶级的意识,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批评人生,来促进社会的变革”43。二文对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等历史概念的娴熟运用印证了1927年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变革的社会学”44所具有的活力和刺激性。正如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所观察到的,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渴望塑造现代社会的命运;同时他们相信未来社会发展的动力秘密就存在于过往的历史之中。45
不过,我们不应该将黄药眠的“文艺”批评简单地视作一种“文学社会学”,或将其对文艺的发展分析看作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图式的粗糙套用。面对“文艺”何以催化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黄药眠选择了一种出其不意的生物学路径:进化论的思路贯穿这两篇文章。
我们现在第一就应该把文艺和其他的社会现象一样放在同一的平面上,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出他的社会原素来,用Physiological method剖明他的进化的阶段来。46
“Physiological method”翻译成中文就是“生理学方法”。“生理学”可被视作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的是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机体的生命现象,而主要研究方法是通过器官系统、细胞组织等层次实验来研究“有机体”功能运作的内在机制。黄药眠对解剖生物机能、生命演化史的执着与他对“创化论”的兴趣一脉相承。柏格森式的生命宇宙设想持续影响着黄药眠,使其在“皈依”马克思的过程中想象出了一种“有机”的艺术进化谱系。前文提到的“生之……”修辞公式在1928年的两篇文章中顺利地转换为一种文艺批评的“生物学隐喻”。在黄药眠对社会组织的观察中,“文艺家”首先是“生之战士”47。在社会进化的视角中,近世文艺是“生之意识”48进化到顶点的产物,其未来的历史目标也是进一步“提高人类的生之意识”49。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来临时,新文学被要求“表现出生之可能”50。尽管这些隐喻所指的“生”的含义并不明晰(后文会分析到),但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到柏格森哲学遗留下的语言惯性。
这类“有机喻体”同样见于黄药眠的文学书写,并通过书信文体转化为一种革命主体的自我指涉。在黄药眠1928年出版的书信体小说《痛心!》中,主人公W君是一个多情的厌世诗人,他渴慕着一个同校的革命者L。在长信中,W君同样以“生之战士”自称,他将阅读英国浪漫主义革命诗人雪莱(Percy Shelley)所引起的内心震荡称作“生之力量”,将坚持书写、生活的意志称作“生之意欲”。值得一提的是,W君与黄药眠自身大学时期的人生轨迹高度重合,这意味着历史现实高度介入了文学想象。51考虑到小说对广州全城戒严、军队叛变、大舰巨炮轰堤等情节的叙述,黄药眠寓意的“革命”更紧密地和1922年“六·一六”武装事变等现实政治投射在一起。52只要我们抽身从历史视域反观,就不难发现,这一场由粤系军阀陈炯明针对孙中山北伐发起的广州兵变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后,孙中山逐渐放弃向地方军阀寻求支持,转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而孙中山用以炮击广州的“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在几年后的“中山舰事件”和“四·一二”事变中彻底凝结为“国共分裂”的历史意象。因而,结合这些“羁留在浅薄的南邦”的记忆书写和小说本身的出版时间,黄药眠笔下的“生之意欲”在与历史巨变的互文中指向了一种“逼上梁山”的革命道路选择。小说中,L经历毕业、兵变等一系列事件后,由“生物学系学生”向“革命家”转变这一身份政治细节十分耐人寻味。它让我们看到,在历经一系列大革命的创伤性事件后,生命成为一种革命的“转换潜能”。这种革命主体的潜力可被浪漫的文学表达、主情文类唤醒。同时,文学本身也好似一种充盈着历史意识的有机物。
因此,综合黄药眠这段时间的“文”与“论”来看,其思想中的“演化生物学”53并没有被轻易地洗去痕迹,而是以一种隐蔽的形式指向了一种活生生的、变化着的文学书写,以及一部充满“生之可能”的变动历史。不过,上述分析还未充分解耦黄药眠文艺理论中“柏格森”和“马克思”的纠缠。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对马克思唯物论进行“复魅”(re-enchantment),才能挖掘其背后复杂的论述逻辑。
将生物世界和人类文化关联起来并非柏格森、尼采等一众生命哲学家的专利——这同样是左翼文艺批评的一项“古老”技能。伊格尔顿早已提醒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存在着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将文化批评系于“生物种属王国”研究上:
从G.V.普列汉诺夫到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以及恩斯特,费舍尔《艺术的必然性》所代表的晚近的奇怪繁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探询中的一支重要潮流。它代表了某种原教旨主义的唯物主义,但也非常有趣,它试图解除唯心主义艺术观的神秘性,把艺术观念放在青年马克思称为“物种的存在”、自然历史或曰物种语境之中。尽管这一潮流表现出实证主义、功能主义和生物主义倾向,它的开阔视野和理论活力仍然与当代左派历史主义的窄小视界形成很大的反差。54
如果我们摆脱一些被后世称为“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机械论魔障,或许有机会重返这种宏阔的生物学视野。伊格尔顿的观察是敏锐的。他让我们注意到“苏联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对于文艺理论的生物学语境贡献——别忘了,他当时也在黄药眠的书架上!根据多年后黄药眠本人的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我是从读普列汉诺夫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开始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列汉诺夫也可以说是我的老师。”55后来他写了《试评普列汉诺夫的审美感的人性论》(1980)批判这位“老师”的美学体系——吾爱吾师,更爱真理——这是后话。

但毫无疑问的是,普列汉诺夫这个常被遮蔽的名字实际上在中国人接触马克思的早期历史中有着相当分量。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普氏对于美学和艺术问题必须“从生物学转到社会学”56的口号为左翼知识分子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这个指向似乎为他们之前隐隐感受到的生物-社会的自觉关联提供了一条明路。57就连不闻理论的鲁迅都被“倒逼”,借外村史郎的日译本翻译出普氏著名的《艺术论》(1930年出版,在其他版本中也被译为《没有地址的信》):“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58
黄药眠也拿起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武装”来对抗进化论之“偏颇”。在《文艺家》一文中黄药眠明确主张:文艺是一种社会现象。“从文学的本身来说他也不过是社会现象之一种,没有社会就没有文艺。故研究文艺,不能把文艺自己划成一个小天地专在他的本身去探讨。”只有解剖其“进化阶段”和“社会原素”,才能把文艺的性质弄清楚,然后才能指明文艺家应该站在什么立足点来批评,他应该表现些什么东西,他是为谁而战。59事实上,这也正是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的根本出发点:“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60普氏当时假设的“论敌”正是生物进化论本身:自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于1895年《物种起源》中提出自然选择以来,文艺活动就被纳入一种生物学的有机形态演变中,文艺被视为一种生物的本能创造。譬如,泰纳的《艺术哲学》也受此趋势影响,像研究动植物那样研究文艺风格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联。而普氏力图在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注意,并非全盘驳斥——论证,美感和艺术的起源并非简单的“自然选择”导致,而是一种“社会劳动”的产物。
为了将作为“物种”的人类从达尔文的自然丛林中夺出来而研究其“历史底命运”,普氏将目光移向人类生活的源头,专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参差的原始时刻,从而构建出关于艺术起源的猜测。他借用达尔文之“根本的对立(anti thesis)”命题来说明美感的艺术表达形式与人类的生产技术、生活劳动之韵律、谐调息息相关。我们借用鲁迅的译序来总结普氏的原始民族艺术研究:
第二篇《原始民族的艺术》先据人类学者,旅行家等实见之谈,从薄墟曼,韦陀,印地安以及别的民族引了他们的生活,狩猎,农耕,分配财货这些事为例子,以证原始狩猎民族实为共产主义底结合,且以见毕海尔所说之不足凭。第三篇《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则批判主张游戏本能,先于劳动的人们之误,且用丰富的实证和严正的论理,以究明有用对象的生产(劳动),先于艺术生产这一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底命题。61
黄药眠显然受到了这种艺术起源论影响。在他的两篇文章中都可见一种对原始共产社会的乌托邦式想象:上溯原始的社会结构、人类的“史前状况”,总能发现一种未经私有财产制度和劳动分工“污染”的古老图景。他摹仿人类学家的语言描绘这幅纯真画面:文艺最初是原始社会劳动之余民众“你一句我一句联续而成的”,是对于饮食、男女、渔猎(我们应注意到,渔猎本身就标志着一种仍未踏入农耕文明的狩猎-采集者的生计方式)、祭祀等内容的歌咏。他还通过对欧洲他者历史的“挪用”说明,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所谓文艺家成了宫廷贵族的附庸,接着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文艺又被第三阶级和小有产者所绑架。由此他得出结论:如今,将文艺还给无产阶级集体是“社会的必然的进程。”所以,“集体化的文学原也不是现在的特创,而只是民众文艺进化的一种再现Recapitulation罢了!”62
黄药眠对“Recapitulation”一词在进化意义上的使用又与生物遗传学形成隐晦对话。这里的跨语际翻译实践藏着一个有趣细节:他并没有使用中文“再现”一词最常对应的英文概念“Representation”,要知道,后者才是与表征、象征等文艺语言问题更加紧密相连的词语,而是故意选择了一个即使在英语中也略显生僻的词语“Recapitulation”。本文认为,这是一种对于知识范畴有意识的选择,因为黄药眠在此所指的恰恰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现”。在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再现”理论(英译即Recapitulation Theory)中,动物胚胎的发育过程会重现该物种远古祖先进化的类似进程。此“重演律”在饱受争议的同时也为生物进化论作出了突出贡献,而“Recapitulation”一词基本在此生物语境中使用。63黄药眠在此将重演“结构”移植到艺术史的发展寓言中,以生命现象催化出了艺术的历史阐释。这种“往日复现”的想象将中国社会的未来与原始大同的“前蒸汽机”景色杂糅在一起。它不仅幻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重返一种“互助”的共产文明,还希望通过“民众心里的热情,民众的勇敢的力量”复现“刚强的、悲壮的、朴素的文学”。在黄药眠看来,“怀古”的集体文学有望消弭个人主义文学,和“灵肉冲突”而“自趋于绝灭”的个人悲剧。64至此,经普氏学说的装扮,社会和阶级方法顺理成章地介入了柏格森的生命世界。
事实上,生命哲学与唯物论在黄药眠这里的有机并置乃至结合并不令人惊讶。如果我们此时返回黄药眠所提及的那篇普氏的引玉之论《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897),就会发现这篇长论其实是对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唯物主义历史观概述》(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1897)所作的书评。65而拉布里奥拉的这部书同时也就是黄药眠常被人忽略的翻译论集《史的唯物主义》(1929)!66我们有理由猜测,正是普氏的批判性介绍使得黄药眠注意到了这个远在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拉布里奥拉——此人正是克罗齐、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一代人的第二国际先师。普氏与拉氏是同时代者,他们“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声相应之处在于对“历史的有机构成”(organic conception of history)67的理解:这种理解根植于二人对原始社会结构的历史阐释,以及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中。我们发现,在黄药眠这个战斗文艺理论家的大脑里,柏格森的生命想象与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的有机历史在并列、反转、错置之间碰撞,由此电光石火之间生产出普罗列塔利亚的火花。
据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1928年后,黄药眠有关“生”的修辞从“生命”“生机”“生存”更多地转向了“生活”“生产”与“人生”。与那些淡出生命哲学的日本同路人们不一样,黄药眠通过接收苏联和意大利的演化生物学批判、文学社会学、唯物历史观从而使生命问题逐渐降落到地表。普列汉诺夫和拉布里奥拉为他带来了更加历史化的视野,他开始通过人类的社会关系处理文艺与生活机制、生产问题之间的勾连,并找到了新的理论语言来阐释艺术和生命的有机演化过程。同时,尽管有着强烈的去神秘化的社会学倾向,黄药眠的文艺批评论述逻辑仍然与生物进化论紧密相关。
03
“约瑟夫的外套”:生命演化与革命突进
尽管普列汉诺夫带来了看起来唯物的、实证的、科学的社会学作为文艺理论的祛魅福音,但生命哲学这个世纪末幽灵却一直徘徊在黄药眠的论述中。生命哲学对自由创造、内在欲力、精神意志的承认正迎合了革命话语对主体构造、能动力量的需求——这也是黄药眠创造社时期保留创化论修辞的原因,同时也是柏格森与马克思产生奇妙化学反应之处。石静远(Jing Tsu)在《失败、国族主义与文学》一书中指出,如果将严复翻译的达尔文《天演论》与张东荪翻译的《创化论》比较,会发现对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分子而言,为抵御外来侵犯而挣扎生存的吸引力已经远低于对一种自身生命欲力的渴望。68正是厨川白村所云“生命力的跳跃和突进”带来了一种希望:文学艺术创造可以爆破,甚至改变自然的演化路线,重新开放人类的命运可能性。这不正是知识分子们对于“革命”——“革除天命”——的终极幻想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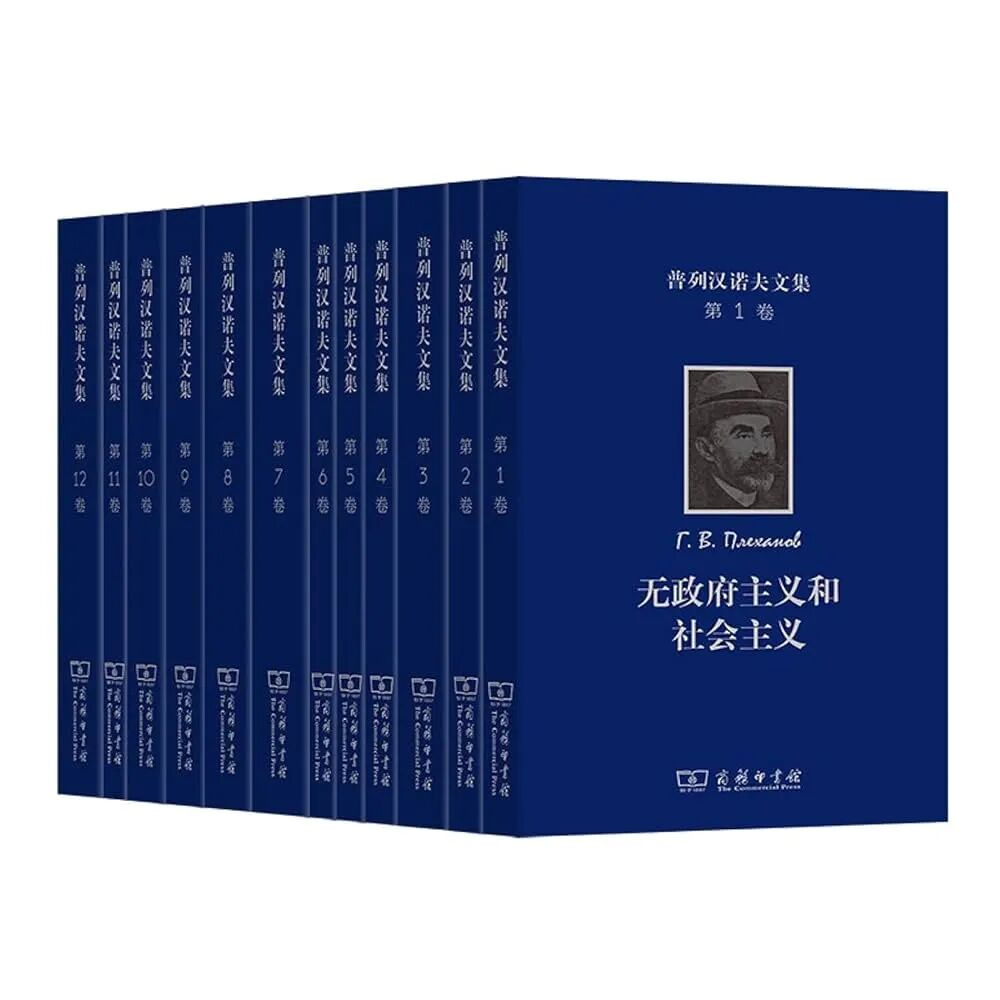
20世纪20年代末期,黄药眠面临的“Evolution”(进化)和“Revolution”(革命)选择并非孤例难题,它是一个有关“社会演化路线”的时代命题。事实上,前面所言笼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概念似乎还不能充分说明其中的纠结。早在1924年到1926年之间,郭沫若与孤军社成员、主张“国家主义”的醒狮派就开始围绕着“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等不同策略展开“笔战”。在这种争论中,他们在生命“演化”与革命“突进”的发展逻辑之间也感到左右为难。
承认社会丛林的自然法则,抑或突进命运放手一搏?这成了一个革命策略问题。根据刘奎的研究,河上肇在《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中就提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根据马克思理论的唯物史观,社会组织之改造(一种社会组织向他种新的更高度的社会组织之推移,即社会革命)决不能实现,因为社会的进行有一个自然法则支配着。当生产力未达到尽头时,社会不能跳过自然的发展阶段。但矛盾的是,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又期待着政治革命之公然爆发。因此,河上肇得出结论:“即是——暂且用不精确的通用语表示时——他们在前是沉着的进化主义者(evolutionalist),在后却又成为狂热的革命主义者(revolutionalist)了。”69
河上肇和他的中国学生们,如郭心崧,都认为“进化论”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根本。而郭沫若则基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现实和列宁主义学说更倾向于直接投入行动的、激进的政治革命。这场论争可被视作1927年后在史学界发生的“社会性质论争”的铺垫和缩影。
在德里克看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混杂性,其关注点摇摆于“历史”与“革命”之间,实际上构造了两种社会模式:“一是社会由动态的相互关联的成分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的‘构造性模式’(structural model);一是阶级斗争决定所有社会构成配置并为历史变革提供终极推动力的‘两极性模式’(bipolar model)。”70前者指向“正常的”历史状态,后者则最适用于革命情势。二者间的差异甚至在“四·一二”事变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中都能找到端倪。71德里克总结的这两个社会模式很有启发。如果我们将其“翻译”成河上肇的生物学譬喻,则此两种社会模式正分别对应了“演化”(evolution)与“突进”(leap)构想。
20世纪20年代演化与突进、生物与社会之间的一系列抵牾,已为黄药眠放弃柏格森这一事件埋下了“隐患”。在《论约瑟夫的外套》(1945)中,黄药眠指出舒芜的“主观论”中所包含的“生机主义”是反唯物论立场的:
可是这个理论虽然十分玄妙,然而却断乎不是唯物论,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原来它把万物的进化都看成是一个最高原则的具现,它是最典型的唯心论!它是唯生史观,它是生机主义,这位先生说的所谓“生生不已的天心”,也可以解释成为生之冲动(Elan Vital)。幸而他还是有意穿上约瑟夫的外套,所以没有把他的“隐得来希”的尾巴全部露了出来。72
这次,黄药眠使用了“唯生史观”这一概念来定义舒芜的有机进化论。这意味着,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生机论、生命哲学作用下,在中国本土已经发展出一套有关“生”的“史学理论”,且其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终于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大裂谷”。即使生命哲学穿上卡尔(马克思)-约瑟夫(斯大林)的外套也无济于事——再也无法遮盖其间的意识形态分裂,以及其内蕴的文艺道路之并峙。虽然黄药眠在此没有明确指出其针对的史学对象,但我们可以根据他在1981年发表的《试评普列汉诺夫的审美理想之生物学的人性论及其他》得出结论:其批判的正是30年代逐渐形成势力的陈立夫。73他在文中提道:“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国民党的陈立夫,把孙中山先生的‘救亡图存’的学说接过去加以歪曲,提出他的所谓‘唯生史观’。生是美,死是丑……再从当时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来看,他这个‘唯生哲学’正是用来诱惑革命者贪生怕死、出卖、投降的哲学。”74
诚如黄药眠的敏锐观察,陈立夫当时主张:“‘生’才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而‘阶级斗争’是人类当进化时,因为物少,不足以维持人类的生存而发生的一种病态。以病态为常态,这是何等可笑的一件事!”75陈立夫这里将阶级斗争归为“病态”,将社会进化归为“常态”的论述就来源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之文本:“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76
“病态”与“常态”之对立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德里克所云“革命”与“历史”、两极性社会与构造性社会之间的摇摆。考虑到陈立夫对从孙中山到戴季陶“民生主义”语系的发挥,不难看出,20世纪4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与生命“玄学”的对峙也是20年代社会性质论争的一次变相延续,而且其对抗强度随着国共合作的彻底分裂、抗战爆发有增无减。对于此时的黄药眠来说,人类历史顺应自然进化这个构想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伪命题。如果继续承认生命的“常规状态”、依旧笃信“众生芸芸各有进机,各不相害,亦各不相让,以成宇宙”77的社会构成,那么中国的阶级革命将无从谈起。同样地,文艺家们如果继续向“内”求生命发展之动力,将美感(在黄药眠的理论体系中也即原始艺术起源)寄托于肉体本能,则得出的文学只能是粉饰和延长历史的工具。这些对生物本能的批判也奠定了黄药眠40年代以后逐渐系统化的美学观念。
余论:面向生活的海洋
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在1926年的文章《当代生机论》(“Contemporary Vitalism”)中如此批评柏格森和杜里舒(Hans Driesch,黄药眠揪住的生物学意义上的“隐得来希”尾巴正出自他):“当代哲学的整个体系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的特殊恐惧。它力图不顾整个历史和社会去开辟另外的世界,并且在有机体的深处挖掘到了这一世界。这是资产阶级世界瓦解和衰落的征兆。”78
这一锋利的谶语,似乎也隐隐预言了生命哲学在革命中国的曲折命运。尽管如此,当年轻的黄花岗诗人黄药眠与生命哲学、共产主义于“十字路口”相遇时,“生”这一词汇还是显示出了惊人的繁殖力。我们在此再借张东荪之言回望这段历史的发生:“本世纪之人间,将开如何生面,真为不可思议”79!在激流涌动的“短世纪”,生命创造问题与演化生物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等知识话语并存、矛盾、对话,显示出不同知识结构在革命主体有意识的选择和斗争中共时存在。
尽管黄药眠后来称那些晶莹腾跃的生命哲学只是他年轻思想的一个荒唐阶段,我们还是不难窥见:他从未捐弃对生命、生活、生机、生产的批判性思索。这也是他对美学美感问题、《费尔巴哈论纲》问题、人道主义论争保持着独特关注的原因。在生命与革命的“奥伏赫变”之间,文艺填充了生物种属王国演化过程中的断裂与沟壑,将历史从准确无误的生与死之间解放出来,从而对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普罗革命者们开放了无限可能。而黄药眠本人则用其一生的行动与书写证明,在历史的大江大河中,他始终“面向着生活的海洋”。
1 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4页。
2 有时也被翻译作“生机”“生机力”“生之冲动”,下文可能交叉使用这几种表述。
3 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第38页。柏格森没有名为《论生命力的冲动》的文章或著作,这里很可能是指以“生命力冲动”为主题的《创造进化论》(1907)一书。
4 从历史的角度看,克罗齐与柏格森在各方面更像是“两条毫无交集的平行线”。参见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Greater Philosophers, New York: Time Incorporated, 1962, p. 434。黄药眠之所以认为克罗齐导源于柏格森,很可能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普遍将克罗齐美学中的意大利语概念“intuizione”和柏格森的“intuition”都翻译为“直觉”,从而使二者在生命哲学方法上看起来互有渊源关系。参见苏宏斌:《论克罗齐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兼谈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的误译和误解》,《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5 黄药眠:《现代文学的流派》,黄大地选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 黄药眠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页。
6 T. S.Eliot ed., “A Commentary”, The Criterion (1922-1939),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67, p.74.
7 黄药眠:《论约瑟夫的外套》,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9页。
8 黄药眠:《论食利者的美学》,同上书,第78页。
9 茅盾:《〈论约瑟夫的外套〉读后感》,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第248页。
10 张历君已经在《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中指出这一问题,比如,就瞿秋白思想研究而言:“主流的瞿秋白研究者基本上抱持着马克思主义与生命哲学相对立的观点”。参见张历君:《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香港中文大学2020年版,第22页。生命哲学研究的代表论著还有彭小妍的《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等,其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思想史和美育运动研究方面,选择对象聚焦在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人生观派知识分子”群体,如张君劢、梁漱溟、方东美等人身上。虽然该书已经提及“创造社”作为文学团体在生机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在细节上是一笔带过的。参见彭小妍:《唯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9年版。
11 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页。
12 张历君:《瞿秋白与跨文化现代性》,第23页。
13 《新辞源》,《文化批判》第1期,1928年1月15日。
14 王璞:《从“奥伏赫变”到“莱茵的葡萄”——“顿挫”中的革命与修辞》,《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5期。
15 刘祎家:《“留声机器”的“奥伏赫变”——再论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论争话语(1926—1928)》,《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8期。
16 Suzuki, Sadami, “THREE THEMES AND A FEW POINTS OF VIEW —for Rewriting of Japa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Literary History”, in Japan Review, 5(1994), pp.125—144.
17 铃木贞美:《日本文化史重构:以生命观为中心》,魏大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
18 同上,第124页。
19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孙猛、徐江、李冬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20 1928年的《流沙》编辑部(包括黄药眠在内)否定了《洪水》风格的旧稿。编者如此描述其旧有特征:“出版部方面交来了一大箱‘洪水’的旧稿,编者如像获得了宝藏似的,高兴得跳了起来。谁想消磨了我好几天的功夫,才令我大失所望。含象征主义味儿的很深的乃超式的诗。带感伤主义色彩很浓的独清式的歌词。穷愁抑郁的所谓徘徊歧途的‘自我表现’,陶醉在老七老八怀中的变态的性欲生活。明酸暗醋的三角恋爱……”参见《后语》,《流沙》第2期,1928年4月1日。
21 黄药眠:《梦的创造》,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第160页。
22 同上,第159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3 彭小妍的研究指出,张东荪对柏格森的翻译以中文创造了一套全新的语汇、修辞和概念。“创造”“直觉”等词汇由此进入中文世界。参见彭小妍:《〈创化论〉的翻译:科学理性与“心”的辩证》,《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要在此说明的是,张东荪的翻译来自英译本,他并不懂法语。
24 张东荪将“目的论”(teleology)译为“究竟观”,他这样总结柏格森的非目的论:“宇宙之真本体乃时间之流动。其作用即绵延之创化。绵延之前,于其果非为目的。”参见张东荪:《〈创化论〉序》,柏格森:《创化论(上)》,张东荪译,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2页。
25 鲁迅译版《苦闷的象征》是黄药眠五四时期阅读过的著作,这一点至少可以在以下文献中得到印证:黄药眠:《谈〈苦闷的象征〉》《现代文学的流派》,黄大地选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 黄药眠卷》,第64—65、215页。
26 Kindler, Benjamin: “Labor Romanticism against Modernity: The Creation Society as Socialist Avant-Gard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2020), pp.43-99.
27 鲁迅:《引言》,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8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第29页。
29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第106页。
30 铃木贞美:《日本文化史重构:以生命观为中心》,第116页。
31 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第3页。
32 鲁迅:《引言》,同上书,第3页。
33 黄药眠:《梦的创造》,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第161页。
34 Pu Wang, The Translatability of Revolution: Guo Moruo and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p.3.
35 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第165页。
36 黄药眠:《梦的创造》,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第164页。
37 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田友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38 程凯:《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9页。
39 特里 · 伊格尔顿:《文化与社会主义》,陈华锋译,《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9期。
40 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第71页。
41 《后语》,《流沙》第2期,1928年4月1日。
42 黄药眠:《非个人主义的文学》,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第165页。
43 黄药眠:《文艺家应该为谁而战?》,同上书,第172页。
44 L.Bramsin, The Political Context of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61, p.21.转引自阿里夫 · 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45 同上。
46 黄药眠:《非个人主义的文学》,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第169页。
47 黄药眠:《文艺家应该为谁而战?》,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第169页。
48 黄药眠:《非个人主义的文学》,同上书,第165页。
49 同上,第166页。
50 同上,第168页。
51 参见黄药眠:《痛心!》,上海乐群书店1928年版。主人公W君在广州大学毕业后遭遇兵变戒严、逃回老家,以及在乡村学校教书之人生轨迹,与黄药眠本人的经历高度重合,可与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第二章第三节“大学生涯”互为印证。
52 黄药眠在广东高师读书时亲历“六 · 一六”武装事变相关的回忆,参见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第39—40页。
53 这里,我使用“演化”这一中立的词汇统称所有和“创化”“进化”有关的综合性生物学学说。这几种学说的具体区分和各自的文化意义将在本文下一节详细讨论。
54 Terry Eagleton ed.,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p.7-8.
55 刘克定编著:《黄药眠评传》,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56 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年]》,《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曹葆华译,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4页。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57 郭沫若回忆:“但自己对于社会科学的要求也早是觉醒了的,就当时耳濡目染地所得来的一些关于辩证的唯物论的学理,觉得好些地方和生物学有甚深的姻缘,例如社会形态的蜕变说似乎便是从生物学的现象脱化出来的。因此便又想一方面研究生理学,而同时学习着社会科学。”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编》,北新书局1946年版,第25页。
58 鲁迅:《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序言”第4页。
59 黄药眠:《文艺家应该为谁而战?》,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第169页。
60 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年]》,《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第308页。
61 鲁迅:《序言》,蒲力汉诺夫:《艺术论》,鲁迅译,光华书局1930年版,第18页。
62 黄药眠:《非个人主义的文学》,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第167页。加粗效果为引者所加。
63 有关海克尔及再现理论在现代中国的影响,参见刘禾:《鲁迅生命观中的科学与宗教(上)——从〈造人术〉到〈祝福〉》,《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期。
64 黄药眠:《非个人主义的文学》,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第168页。
65 普列汉诺夫:《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曹葆华译,生活 · 新知 · 读书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59页。普氏开篇就完整引用原著:Essais sur la conception matérialiste de l’histoire par Antonio Labriola, professeur à l’université de Rome, avec une préface de G.Sorel. Paris, 1897。该书评以“卡缅斯基”的笔名发表在彼得堡出版的文学和政治月刊《新语》杂志1897年9月号上。黄药眠则在《史的唯物主义》的“译后记”中表示,自己翻译的是Charles Kerr出版社的英译本Essays on the Materialsit Conception of History,只是删去了第一篇总论。参见黄药眠:《译后记》,Labriola:《史的唯物主义》,黄药眠译,上海江南书店1929年版,第209页。
66 Labriola:《史的唯物主义》,黄药眠译,上海江南书店1929年版。
67 Labriola, Antonio, Essays on the Materialsit Conception of History, trans. Charles H. Kerr, Chicago: Charles H.Kerr Co-Operative, 1908, p.54.
68 Jing Tsu,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08.
69 参见刘奎:《郭沫若的翻译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1924—1926)》,《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5期。
70 翁贺凯:《译者的话》,阿里夫 · 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第4页。
71 德里克指向的是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和斯大林(Joseph Stalin)在中国社会结构论调上的分歧,同上书,第53页。
72 黄药眠:《约瑟夫的外套》,陈雪虎、黄大地选编:《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第237页。加粗效果为引者所加。
73 根据肖伊绯的研究,“唯生史观”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蔡元培1928年的演说《说总理的惟生史观》。因而,陈立夫应当不能算此学说的最早创立者,但他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参见肖伊绯:《蔡元培:首倡“唯生史观”——以新近发现蔡元培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讲演稿为中心》,《关东学刊》2018年第5期。
74 黄药眠:《试评普列汉诺夫的审美理想之生物学的人性论及其他》,《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3期。
75 陈立夫:《唯生论》,重庆中正书局1939年版,第74页。
76 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三民主义》,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305页。
77 张东荪:《〈创化论〉序》,柏格森:《创化论(上)》,第3页。
78 B.H.沃洛希诺夫:《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巴赫金全集》第一卷,钱中文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该书发行伊始并未按照本名发表,而是以巴赫金朋友名义署名沃洛希诺夫。参见Valentin Voloshinov, Freudianism: A Marxist Critique, trans. I. R.Titunik,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2。
79 张东荪:《〈创化论〉序》,柏格森:《创化论(上)》,第3页。加粗效果为引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