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云:“中国政治最高的是‘礼’,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礼治。”[1]可见礼法制度是政治的根本,其中丧服制度事关人伦的安排,是重中之重。丧服制度既包括经典文献《仪礼·丧服》中的条目,也包含后世的创制。在经典的制度化中,儒家学者的议礼学说起了关键的作用。名儒议礼莫盛于晋朝,徐乾学云:
古今议礼之家莫详于晋,亦莫善于晋,其时庙堂之上,学士大夫各执经以立论,咸灿然可观,实后代所不及。如后母之子为前母制服,及父母不知存亡,子行丧制服之议,事出创见,礼所不及者,亦皆辨之成理,可为后世遭变礼者之准。如此之类,咸为采入,以继于《礼经》之后,庶几处礼之常者,既有所考见,而处礼之变者,亦得以折衷云。[2]
徐氏认为,虽然《礼经》有极其详细的服制条目,但现实生活中仍有许多变礼。如《丧服》中无“前母”的概念,晋代却出现了“后母之子为前母制服”的案例。[3]这就需要学者依据《礼经》的原则进行推论,并给出合理的裁断。对于变礼的折衷,不仅解决了当世的问题,更给后世“处礼之常者”提供参考,深化对于《礼经》原则的理解,故而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收录了大量的议礼之文。
除了“事出创见”的变礼之外,现实政治中更有直接违背《礼经》原则的议题,如“反向为后”问题。晋元帝令庶子司马晞出继武陵王喆,后至晋穆帝时,晞母薨逝,时为武陵王的司马晞为本生妾母当制何服,却成了棘手的问题。因为《丧服》中只有小宗之子出继大宗的规定,[4]以卑继尊,而天子庶子出继诸侯王则是“反向为后”,是非礼的。而出后之庶子为其本生妾母制服,又涉及余尊厌、出降、庶子为后“妾母私亲妨祭”等问题,就格外的复杂。诸家之论,以及诏书所定,都力图为“非礼”之礼提供圆满的解决方案。本文试图探讨诸说背后的学理以及皇权对礼学原则的入侵。
在探讨“反向为后”中的妾母服制前,有必要对一般为后中的本生妾母服制做一个梳理。此即庶子为人后者为其母的服制,然而《仪礼·丧服》中没有直接的规定,只能通过相关条目进行推演。具体来说,是由庶子为妾母之服、庶子为父后者为妾母之服,推出庶子为人后者为妾母之服。
首先是庶子为妾母之服。按照士制,庶子为妾母之服即是平常的母子之服,父在为母杖期,父没为母齐衰三年。若是大夫以上之制,还有厌降以及余尊厌的问题。
(《大功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传曰:何以大功也?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则从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郑注】公之庶昆弟,则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则父在也。其或为母,谓妾子也。言从乎大夫而降,则于父卒如国人也。[5]
(《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既葬除之。
【郑注】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为母,谓妾子也。诸侯之妾子厌于父,为母不得伸,权制此服,不夺其恩也。[6]
由上所引《丧服》经传及郑注可知,大夫之庶子、诸侯之庶子为其母服丧,受到父亲的厌制。其中大夫庶子为其母,父在时受到厌降,由齐衰杖期降一等至大功,此即郑玄所云“大夫之庶子,则父在也”;父没后则厌降解除,仍服母齐衰三年,此即郑玄所云“父卒如国人也”。若是诸侯之庶子,则厌降的程度更深,父在时,庶公子为其母在五服外,仅服“练冠、麻(绖带)、麻衣縓缘”;父没后,仍受到父亲余尊的厌制,[7]为母仅服大功。天子、诸侯厌降的制度相同,则天子之庶子为其母,也是父在厌降至五服外,父没余尊厌至大功。
其次,若庶子为父后,则为母仅服缌麻,其制服原理是“私亲妨祭”原则。
(《缌麻章》)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传曰:何以缌也?《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然则何以服缌也?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因是以服缌也。[8]
所谓“庶子为父后者”,即是以庶子的身份继承父亲的宗庙祭祀之权,且此时父亲已经去世。由于父、祖等“尊者”的祭祀由自己主持,庶子因主祭而“与尊者为一体”。既然如此,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的服制,也应当从父、祖等“尊者”的角度考虑,而不是从己身的角度考虑。自父亲言之,母亲仅为妾,与父亲并非是“夫妻一体”关系,父不服妾。所以庶子与妾母虽然在血缘上是“母子至亲”,但庶子“与尊者为一体”,则妾母之于子,只能算“私亲”。对于“私亲”的概念,张锡恭有详细的辨析:
凡私亲与私尊不同,適妻之子,父在称其母为私尊者,以己所独尊,而非父之所尊也。父虽不以为尊,而固以为至亲,则非私亲矣。故父在为母,服期之至重者,杖而菅屦,父卒则三年。虽废祭而无以嫌于父之至亲,而非己之私亲也。[9]
张氏区分了“私亲”与“私尊”两个概念。“私尊”指的是父之適妻,由于父为一家至尊,父之適妻屈于父,虽为子女所尊,只能算是“私尊”。然而“私尊”来源于“夫妻一体”的“至亲”关系,父之適妻是父亲之“至亲”,才能成为子女之“私尊”,[10]也因为“夫妻一体”而尊卑与夫相同。[11]又按照礼之通例,吉凶不相干。祭礼属于吉礼,而丧礼属于凶礼,两者矛盾。適妻与夫同尊,故而宗庙祭祀应该让位于適妻之丧。但是妾的地位低微,不能因为妾母之丧而影响尊者的祭祀,故庶子为父后者本不应为妾母服丧。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庶子无服终究于情不忍,恰好在祭礼中有遇到“死于宫中者”三月废祭的旧例,则可据此为妾母制服缌麻三月。这就是妾母服制中的“私亲妨祭”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服缌麻,对比一般的父没为母服齐衰三年,好像类似厌降,实则与厌降毫无关系,张锡恭云:
《丧服经·缌麻三月章》:“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按,此降其母在缌,类于厌矣,而非厌也。何以言之?凡以厌而降者,皆降一等。为母齐衰三年,而以父在屈,则齐衰杖期,降一等故也。士之庶子,父在为母杖期,大夫之庶子,父在为母大功,降一等故也。而此降其母至缌,则非降一等之比矣。云为父后者,指父卒者言也。父卒而有余尊之厌者,惟天子、诸侯之庶子耳,大夫、士之庶子无之矣。大夫、士庶子,父卒为母,皆得申其三年者,以无余尊之厌也。而此为其母缌,兼君、大夫、士之庶子,则非余尊所厌之比矣。吾故曰:类于厌而非厌也。既非厌矣,何以服缌麻三月也?则传言之矣。传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又曰: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因是以服缌也。因礼本有三月不举祭之例,而制三月之服,则不能有加于三月者,恐废祭故也。要而言之,不敢以私亲之丧而废正尊之祭也。[12]
张氏认为厌降是伴随爵尊而来的,士之爵位低微,没有厌降。大夫之爵稍尊,故而有厌降,降服的幅度是较士制降一等。天子、诸侯之爵更尊,故而厌降的程度更大,于大夫降一等的亲属,天子、诸侯则绝而不服,甚至在死后还对儿子有余尊厌。然而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服缌麻的制度,囊括了天子到士的所有阶层,与厌降仅属于大夫以上阶层不同。同时厌降的幅度,大夫是降一等,天子、诸侯则是绝而不服。而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是从齐衰三年直降至缌麻,既非降一等,又非全然无服,又与厌降有异。所以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缌麻的原因不在厌降,而是“私亲妨祭”,只要庶子有主祭之权,妾母便是“妨祭”,与厌降毫无关系。
再次,是庶子为人后者为妾母之服。张锡恭进一步认为,庶子为父后中的“私亲妨祭”原则,可以延伸至庶子为人后者为妾母的服制。张氏云:
(“私亲妨祭”原则)非惟为父后者为然也,虽为人后者亦然。后大宗者为本生母期,以本生父谓为至亲,则非己之私亲也。若妾母之子后人,则不服期而服缌矣,非惟己所生母为然也,虽父所生母亦然。父所生母似不可为私亲,而与先祖祀事相衡,则祀事不可阙,而无异于私亲也,亦服缌而已矣。然则所以服缌者,恐废祭而非厌,昭昭然矣。[13]
庶子为父后者,其妾母之丧妨碍父、祖等“尊者”之祭祀。庶子出后大宗宗子,依据“为人后者为之子”的原则,[14]则祭祀的“尊者”由小宗序列的父、祖变为大宗序列中的父、祖,妾母在本生小宗中是“私亲妨祭”,现在在大宗序列中依旧是“私亲妨祭”,故可以由庶子为父后推论庶子为人后的情况。而且张锡恭甚至认为,凡是妾,无论是己之母或是父之母,从祭祀“尊者”的角度看来,都属于妨祭的“私亲”,故而都仅制缌麻之服。
张锡恭的推论无疑是正确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推论背后有严格的尊卑次序的考虑。为父后者的“尊者”指父亲、祖父、曾祖、高祖等小宗一系的祖先。为人后者的“尊者”指所后大宗宗子一系的祖先。根据“尊祖故敬宗”的义理,历代大宗宗子代表的是太祖,则大宗一系的“尊者”直指太祖。曹元弼云:“高、曾、祖、祢皆是尊,而太祖为尊中之尊。”[15]既然太祖之尊高于小宗的“尊者”,那么代表太祖的大宗也高于小宗。庶子为父后,其母作为“私亲”尚且妨碍小宗的祭祀,那么庶子为人后者,其母更加是妨碍大宗祭祀的“私亲”。同处一族,“尊者”愈尊,使得“私亲妨祭”原则可以通用,也确定了庶子为人后者为其母缌麻的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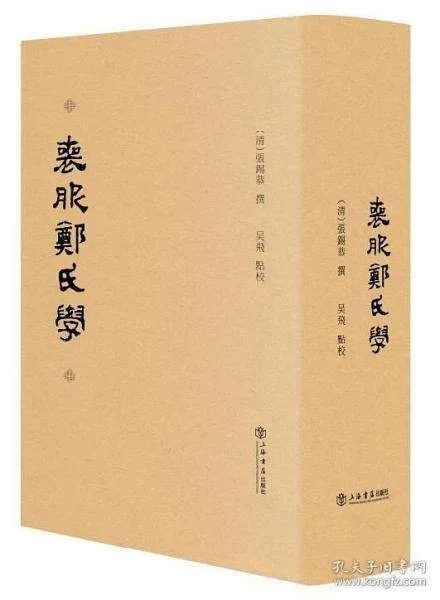
由上文的推演可知,大宗尊于小宗的前提,使得我们在庶子为人后者为其妾母的服制问题中,只需要延续“私亲妨祭”的原则,不必考虑其他因素。这不仅是一个方便法门,更重要的是否定了另外一条理论路径,即“出降解除厌降”。因为这条路径在“反向为后”中将会死灰复燃,故而很有必要做一下说明。
何为“出降解除厌降”?上文已经提及,在大夫以上的制度中,庶子为妾母服丧,还涉及到厌降、余尊厌等问题。如大夫之庶子,父在时受到厌降,为妾母由齐衰杖期降至大功,父没则厌降解除,为妾母得伸齐衰三年。天子、诸侯之庶子,父在时受到厌降,为妾母之服在五服外,父没后仍有余尊之厌,而为妾母服大功,不得伸三年。其中余尊厌属于广义的厌降范畴。[16]《丧服传》对于厌降的经典表述是“大夫之庶子,则从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17]“君之所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18]均是子受父厌而降服死者,故黄以周云:“厌降者惟厌其子。”[19]则厌降只存在于父子之间。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论,父为子之天,如果子“所天”者发生了变化,则基于父子关系的厌降,也应该随之解除。按照这个假设,为人后者就意味着父子关系的改变,那么本生父亲的厌降或者余尊厌就应该解除。以诸侯庶子为例,既然为人后,则本生父之厌降或余尊厌即应解除,为妾母的服制变为父在杖期、父没齐衰三年。另一方面,厌降的解除来源于出后,有“不贰斩”以及降本宗亲属一等的规定,故而为本生妾母的服制还应该出降一等,至齐衰不杖期。这就是“出降解除厌降”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到,按此思路,制服的结果不是缌麻,而是齐衰不杖期。在反向为后的讨论中,许穆和崧重即持此种观点,而孔恢则从反面进行推演,可见这一思路是议礼的关键。那么这个思路有何根据?为何不能在一般为后中适用?又为何会在反向为后中抬头?是值得考察的。
“出降解除厌降”的思路来源于庾蔚之对于“公主服所生”的讨论。
庾蔚之云:“公主为其母,应周。何以言之?在室有余尊之厌,服不得过大功,故服母及兄弟,不得有异。既出则无厌,故为母得周。所以知既出则无厌者,礼,尊降、出降,亲疏不异,尊降唯不及其嫡耳。至于厌降,唯子而已。在室,父在为母周;既出,服母与父同。是故知既出则无厌也。又,正尊不报,礼之大例。而女子适人,父报以周,使其移重于夫族,推旁亲也。以此推之,出则无厌,理据益明。”[20]
所谓“公主服所生”,即是公主出嫁后为其本生妾母的服制。庾蔚之认为,公主在室时,若父在,则受厌降而服妾母“练冠、麻、麻衣縓缘”(在五服之外),父没之后仍有余尊厌,为妾母仅服大功。然而出嫁之后,公主的“所天之人”由父亲变为丈夫。既然不再“从父”,那么基于父女关系的厌降就解除了,可依据士制女子子适人者为其母,服齐衰不杖期,此即“既出则无厌”。庾蔚之为此还提供了一些论据,但是这些论据是错误的。[21]张锡恭则重新解释了庾蔚之的观点,认为:“女子……体于夫,不复体于父,妇人不能贰尊之谊也。庾氏所论,陈义甚精。”[22]所谓“体于夫,不复体于父”,即女子“所天之人”随着出嫁而发生了变化,由“在家从父”变为“出嫁从夫”,接下来的都依据夫家的标准调整亲属关系,那么“在家从父”时的厌降或余尊厌,就应当解除。从这个角度论证公主“既出则无厌”,是非常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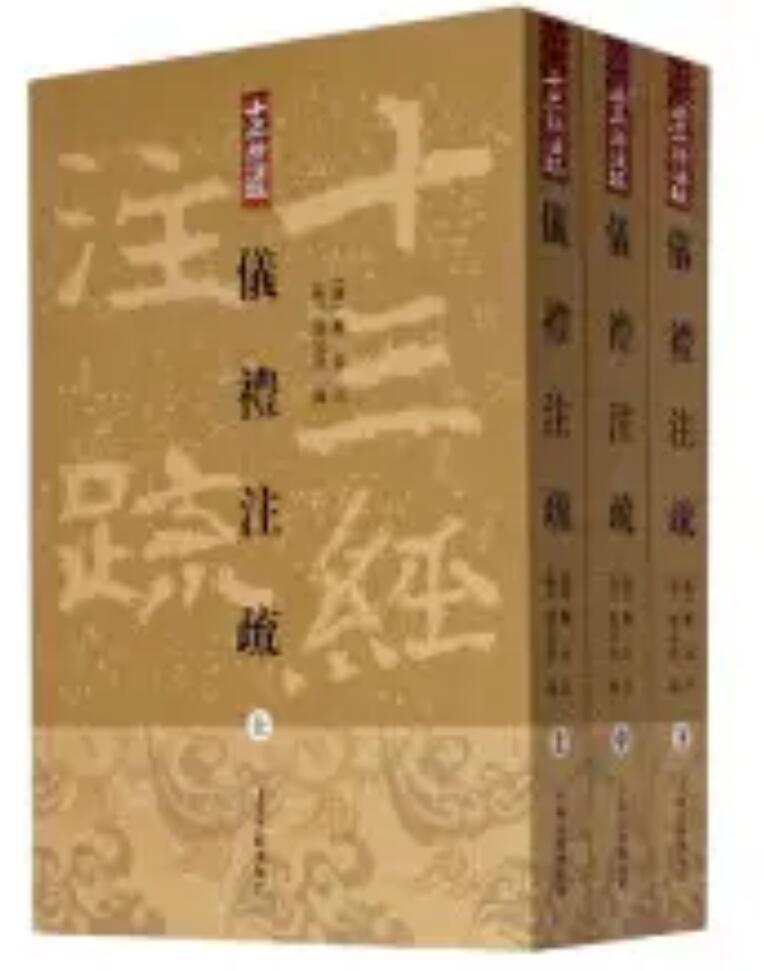
然而“既出则无厌”的思路不适用于为人后者的情况。虽然按照郑玄的分类,为人后者和女子子都属于“出降”,都有“不贰斩”,“所天之人”皆非己父,[23]似乎“既出则无厌”的逻辑可以推至为人后者。但是为人后者的“出降”与女子子的“出降”有巨大的差别。女子是出嫁外族,身份发生了巨变,本族尊厌之制自然不再适用于外嫁之女;而且女子出嫁是必然之事,不必计较父与夫爵尊的高低。[24]但出继是或然之事,发生在宗族内部,而且一定要比较本生父亲与所后者的尊卑,所以《丧服传》规定,唯有大宗才能立后,小宗不可以立后,曹元弼云:
古者大宗立后,小宗无子不立后,明非临以太祖之尊,无离人父子天性之道也。故传曰:“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大宗必立后者,大宗者尊之统,敬宗所以尊祖,故不得已而离己之父母以后之,后之者与所后者为父子,而持重于其宗也。[25]
为人后就意味着破坏“父子天性”,小宗之间是平等的,不能因己之无后,而破坏他人的“父子天性”,所以小宗不能立后。但是太祖之尊可以“离人父子天性”,而大宗代表的是太祖的统绪,“敬宗所以尊祖”,故而大宗能够立后。依照这个逻辑,所后者必然尊于本生父亲。而且为后发生在宗族内部,即便本生父亲的厌制随着出继解除了,但从所后父的角度看来,本生妾母理应受到更强的厌制,根本不会解除厌制。所以在一般为后中不会采用“出降解除厌降”的逻辑,而是延续了“私亲妨祭”的原则。另一方面,这一切都是基于小宗之子出继大宗,所后父尊于本生父的前提。如果颠倒过来,大宗之子出继小宗,本生父尊于所后父,那么“出降解除厌降”的逻辑就可能死灰复燃,因为所后父能否厌制本生妾母是存疑的。
四、反向为后中的妾母服制
由上可知,在一般的为后关系中,遵循着大宗高于小宗的逻辑,一旦出继,就默认了本生父为小宗,就有了“出降”,又默认了本生妾母的“私亲”身份,而为之服缌,而所谓的厌降逻辑是不成立的。而在反向为后中,本生父的爵位高于所后父,甚至本生妾母都与所后父的地位相当。如晋代的司马晞本晋元帝庶子,却出后武陵王,尊卑倒置,属于非礼的行为。在非礼的前提下,诸儒讨论司马晞为本生妾母之服,想要寻求一种合礼的解释。就牵涉到一系列礼学原则的交锋,如反向为后中是否还有“出降”?妾母的“私亲妨祭”推论是否还能运用?被遮蔽的厌降逻辑是否能够抬头?而且不同的处置方式背后,更彰显了皇权侵入礼学原则的深浅程度,下面我们具体分析。此次议礼的记载见于《通典》。
穆帝升平中,太宰武陵王所生母丧,表乞齐缞三年;诏听依昔乐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26]
太宰武陵王即是司马晞,本晋元帝庶子,却出后当时的武陵王司马喆,[27]至晋穆帝升平(357-362)中,本生妾母薨逝,司马晞表请服齐衰三年,诏书则认为应该按照乐安王故事,服大功九月。乐安王司马鉴为司马昭之庶子,生母身份低微,《晋书·文六王传》云:“不知母氏。”[28]晋武帝践祚,追赠父亲司马昭为文皇帝,封司马鉴为乐安王,则乐安王服其生母,受到文皇帝的余尊所厌,[29]故而服大功九月。我们可以看到,司马晞所请的齐衰三年,与诏书所定的依乐安王故事,看上去都是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30]如齐衰三年是士制父卒为母之服,没有考虑到天子庶子的身份,也没考虑妾母问题、为后问题,更别说是“反向为后”;而乐安王故事,则是一般意义上的天子庶子服妾母,没有出继的问题,更未涉及“反向为后”的复杂情况。而儒者学士们的议礼,显然要顾及这些复杂的问题,首先发言的是孔恢。
太常江夷上博士孔恢议:“礼云:‘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缌。’又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为母九月。’郑云:‘君卒,子为母大功。大夫卒,子为母三年。’经文则一,而郑有二。疑[31]太宰若从三年之制为重,则应从九月,无应从缌麻之理。且太宰以天子之庶出继诸侯,本无应厌降之道。太宰今承诸侯别祀,又不同庶姓相后,有承继大宗之义,应从降一等之制。从九月亦降一等,应服五月。出后者之子,亦皆还降其本亲祖父母、伯叔一等。[32]又礼无蕃王出后本亲与庶姓有异之制。” [33]
孔恢主张太宰武陵王为本生妾母服小功五月,他的逻辑是余尊厌迭加出降。首先,孔氏注意到了这是“反向”的为后,虽然太宰出后诸侯王,要以诸侯王为父。但由于是反向为后,太宰的生父是天子,所后父是诸侯王,尊卑倒置,他想到的处理方式是保留太宰元帝庶子的身份,并以之为立论的起点。这样,厌降原则就再次抬头,当时晋元帝已经驾崩,太宰仍受到余尊厌,为妾母服大功,故孔恢认为太宰“应从九月”。其次,在余尊厌的基础上再叠加出降。孔恢云:“太宰以天子之庶出继诸侯,本无应厌降之道。”此处“厌降”二字颇难解释,孔氏前面认为太宰当以大功作为理论起点,则认同了“厌降”逻辑,此处又言“无厌降”,这是矛盾的。联系下文都是谈论“出降”问题,则此处“厌降”应该理解为“出降”。这是说,反向为后中的尊卑倒置,本生父是天子,所后父是诸侯,要是彻底贯彻尊卑上下的差别,就没有出降本生父的道理。虽然出后诸侯王,仍保留天子庶子的身份,行余尊厌之制。这个可以称作“出而不降”,也是诏书依乐安王故事的用意。但是孔恢却做了调和,认为“太宰今承诸侯别祀”,“有承继大宗之义,应从降一等之制”,则是把诸侯王强行的设定为大宗,天子设定为小宗,附加了“出降”一等,故得出小功五月的结论。然而保留天子庶子地位和出降一等的逻辑显然是矛盾的,只能说孔氏是在贯彻皇权的基础上,对于皇权作了一定的削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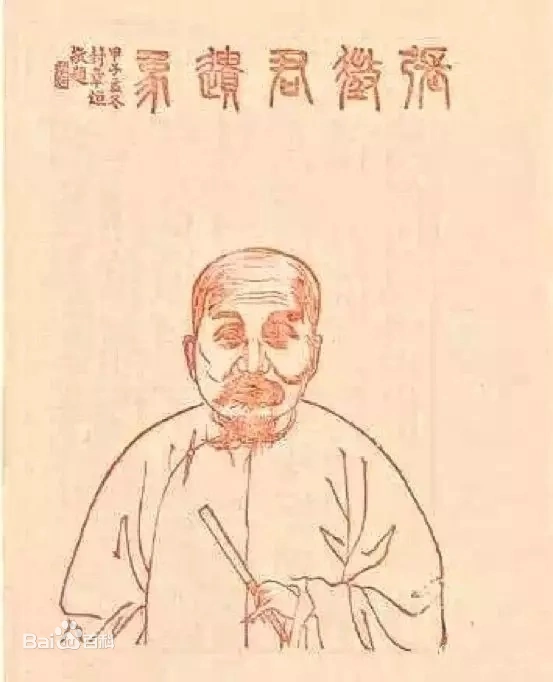
而谢奉和曹处道则完全从正常的为后原则出发,认为太宰当服缌麻。
尚书谢奉:“按礼,为人后者三年,必以尊服服之。庶子为后,为其母服缌。传曰:‘何以缌?与尊者为体,不敢服其私亲。’礼唯大宗无继支属之制。太宰出后武陵,受命元皇,则纂承宗庙,策名有在,礼制既明,岂容二哉!夫礼有仰引而违情者,故有君服而废私丧。屈伸明义,非唯一条,所谓以义断恩。况贵贱之礼既正,岂得不率礼而矫心。当依庶子为后之例,服缌而已。”[34]
祠部郎曹处道云:“礼,庶子为父后,为其母缌,与尊为体,不敢伸恩于私亲。为人后,以所后为父,亦是尊者为体;其所生母,俱是私亲。为父后及为人后,义不异。”[35]
首先,谢奉对于反向为后作了拨乱反正的工作,认为只有小宗出继大宗,大宗不得出继小宗,此即“礼唯大宗无继支属之制”。天子庶子出继武陵王则属于非礼,而且非礼的后果应该由天子承担。既然确定了为后之事,就应该遵守一般为后的法则,以小宗继大宗,那么天子就自居于小宗的地位。谢氏所云“受命元皇,则纂承宗庙,策名有在,礼制既明,岂容二哉”就是这个意思。其次,既然天子自居小宗,那么尊卑次序就排定了,武陵王喆作为大宗尊于天子(因天子自居小宗),而司马晞之母是小宗的私亲,则更是大宗的私亲,故而可以依据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之服推论为人后者为妾母之服,最终制服缌麻。可以看到,谢奉和曹处道的处理方式,是在源头上纠正“反向为后”的错误,完全按照礼学原则推论,逻辑一贯,故而张锡恭云:“谢奉、曹处道等议,援此经(指“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为例,谓当服缌,其议是矣。”[36]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议中,皇权丝毫没有干预到礼学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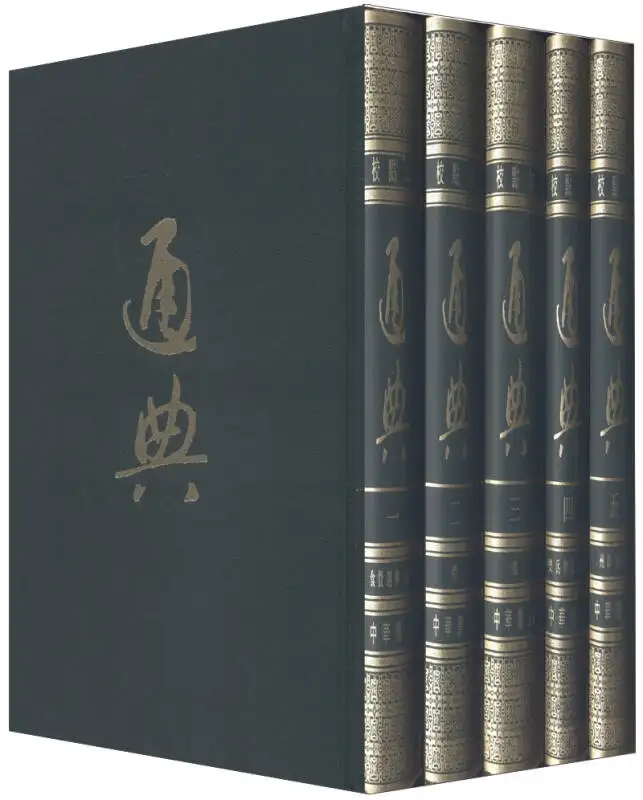
图为《通典》书影
而许穆和崧重则从“出降解除厌降”的角度调和反向为后中的矛盾,认为太宰当服不杖期。
仓部郎许穆议:“母以子贵。王命追崇夫人,视公爵,秩比诸侯。凡诸侯之礼,服断旁亲,以国内臣妾并卑故也。姑姊妹女子子嫁于诸侯,则各以其服服之,尊同故也。卑则服阙,尊则礼行。太宰封王,继于蕃国,出离其本,仰无所厌。夫人、诸侯,班爵不殊,缘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厌,薄出礼之降,制服周可也。”
吏部郎崧重议云:“考之礼文,太宰应服齐缞周。今以《春秋》条例以广其喻。母以子贵,庶子为君,母为夫人,薨卒赴告,皆以成礼,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风是也。此则身为父后,服应缌麻,犹以子贵,得遂私情,经有明文,三传不贬,况于太宰贵,同古例不为父后者耶?[37]且礼有节文,因革不一。自汉以来,皇子皆为始封君,始封君则私得伸。设令太宰不出后,必受始封,服无厌降。出后降一等,复何嫌而不周乎?”[38]
许穆认为,虽然太宰出继诸侯王,但如果纯粹将天子放在小宗的位置,又用私亲妨小宗祭祀推论私亲妨大宗祭祀,则皇权受到了太多的抑制,有损尊尊之义。故而进行一个折衷:首先肯定“出降”的合法性。因为太宰出后武陵王属于既定的事实,而为后就默认了大宗高于小宗,故而天子仍然自处小宗地位,故有“出降”。其次,打断“私亲妨祭”由小宗推向大宗的逻辑,以此彰显皇权。认为太宰之母虽然是天子之妾,但与诸侯王相较,两者的地位相等。所以司马晞之母在天子之处可以视为“私亲”,在诸侯王处则是爵尊相同,不能视为“私亲”。再次,“私亲妨祭”的逻辑走不通,则厌降的逻辑重新抬头。太宰出后武陵王,不再以晋元帝为父,则基于“父子一体”的余尊厌被解除,太宰应服其母齐衰三年,此即“缘天然之恩,伸王子之厌”。同时,出后是余尊厌解除的前提,故而还要叠加“出降”,所以太宰为其母当服齐衰不杖期。当然,许穆和崧重的说法是有很多问题的,比如用《春秋》“母以子贵”来证明妾母尊同诸侯是不恰当的。[39]许穆“薄出礼之降”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出礼之降”并未“有薄”,否则太宰当为妾母服齐衰三年,而非不杖期。但这些错误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天子之妾尊比诸侯,这个属于皇权的延续。许穆、崧重的用意是,一方面在承认“出降”的前提下,天子不得不自居小宗的位置,另一方面通过天子之妾尊同诸侯,诸侯王不得厌制天子之妾,就不能援引“私亲妨祭”原则,定妾母之服为缌麻,以此保留皇权之尊,但这两种处理始终是矛盾的。
五、结语
可以看到,“反向为后”本身是非礼的,诸儒探讨其中的妾母服制,都试图找到“非礼之礼”,为此提供完满的解释。这些解释运用的礼学原则不同,皇权侵入礼学原则的程度各异。其中诏书主张的大功说和谢奉、曹处道主张的缌麻说是两个极端。前者完全遵循尊卑次序,既然天子尊于诸侯,那么天子庶子出后诸侯王时,就没有“出降”,仍保留王子身份,太宰根据余尊厌原则为妾母大功;后者完全遵循一般为后原则,将天子彻底放在小宗的位置,以“私亲妨祭”逻辑处理妾母服制,最终制缌麻服。而孔恢主张的小功说和许穆、崧重主张的不杖期说,都属调和之论,前者是以皇权为前提,部分保留为后法则,即在保留天子庶子身份的前提下,再迭加出降,即由余尊厌的大功,再出降一等至小功;后者是以为后法则为前提,适当保留皇权之尊,即首先承认出降,再以天子之妾位同诸侯,阻隔“私亲妨祭”原则的扩展,最终定为不杖期。但两说在学理上始终是矛盾的。同样的,孔恢的调和之论也是矛盾的,先以余尊厌体现皇权,又在此基础上叠加出降,又以小宗视天子,最终制服小功。至于太宰自请的齐衰三年,逻辑上更加混乱,首先是由出后而解除余尊厌,为妾母三年,反过来又不承认出后中有出降,仍保留齐衰三年,这明显是徇私情的作法,故而诸儒皆不取。
而这次议礼最终的结果是“诏常侍割喻太宰,从缌麻服制。累表至切。又遣敦喻。太宰不敢执遂私怀,以阙王宪,乃制大功之服。”[40]诏书初令太宰服大功,此处却在缌麻和大功之间做了摇摆,最后太宰制大功之服。自太宰而言,难免夹杂对于母亲的罔极之情,丧服能重则重。从制度上而言,“反向为后”本来就是皇权对于礼制的破坏,最后也选择了一个最符合皇权尊尊之义的结果。
註釋:
[1]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80页。
[2] 徐乾学:《读礼通考》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页。
[3] 具体的论述详见吴飞:《王昌前母服议》,载吴飞主编:《婚与丧:传统与现代的家庭礼仪》,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165-211页。
[4] 《丧服传》云:“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表明只有大宗宗子才能立后。参见《仪礼注疏》卷三〇,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1106页。
[5] 《仪礼注疏》卷三二,第1114页。
[6] 《仪礼注疏》卷三三,第1120页。
[7] 关于“余尊厌”的详细考证,可参看拙文《略论中国古代丧服制度中的旁尊降与余尊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30-39页。
[8] 《仪礼注疏》卷三三,第1119页。
[9] 张锡恭:《丧服郑氏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标点本,第894页。
[10] 张锡恭以为,母亲成为子女“私尊”的前提是父亲的“至亲”,若非父亲的“至亲”则只能是子女的“私亲”。张氏的这个论断是有条件限制的,仅针对庶子为父后的情况。若庶子不为父后,母亲即便不是父亲之“至亲”,也可以成为子女的“私尊”,如士妾之子为其母,父没后仍服齐衰三年,大夫庶子为其母,父没亦是齐衰三年,而齐衰三年是“私尊”之服。所以说“私亲”这个概念仅限于庶子为父后者或为人后者,在涉及“尊者”祭祀的时候才是成立的。母亲之“私尊”也不必然的同父亲之“至亲”联系在一起。
[11] 《丧服传》云:“夫尊于朝,妻贵于室。” (参见《仪礼注疏》卷三一,第1109页)可证夫妻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尊卑相同。“妨祭”问题涉及的是夫妻整体的尊卑,若夫之丧妨祭,则妻之丧亦妨祭。若析言之,家无二主,夫尊于妻,这是小家庭内部的尊卑问题,与“妨祭”无关,故而不在讨论之列。
[12] 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第893-894页。
[13] 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第895页。
[14] 《丧服传》云:“(为人后者)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见《仪礼注疏》卷二九,第1101页。
[15] 曹元弼:《礼经校释》,《续修四库全书》第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3-404页。
[16] 如黄以周言:“余尊即厌降。”参见黄以周:《礼书通故》,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标点版,第306页。 孙诒让亦云:“(余尊厌)实即四品中之厌降也。”参见孙诒让:《籀庼述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标点版,第79页。
[17]《仪礼注疏》卷三二,第1114页。
[18]《仪礼注疏》卷三二,第1115页。
[19] 黄以周:《礼书通故》,第305页。
[20] 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标点版,第2204-2205页。
[21] 庾氏的论据有两条,第一,女子子在室时,为母服齐衰杖期,齐衰杖期相对父没后为母齐衰三年而言,是属于厌降,适人后为父母同服齐衰不杖期,是厌降的解除。第二,女子子在室时,受到父亲的正尊降服(即女子子为父服斩衰,父则为女子子服不杖期,两者有等差),这属于厌降,出嫁后则父女互服不杖期,再无等差,这也是厌降的解除。但这些论证是错误的。如庾氏认为,父在为母齐衰杖期,相对于父没为母三年来说,属于厌降。这是错误的,因为厌降伴随爵尊而来,是大夫以上之人针对士服(即本服)的降服,父在为母杖期属于本服,本服无所谓厌降。庾氏又认为女子出嫁后为父母同服齐衰不杖期,也属于厌降的解除。但是上文已经证明,父在为母服杖期是本服,本非厌降,又何来厌降之解除?故而也是错的。此外,庾氏又认为女子子出嫁后,父亲与女子子之间是报服。这也是错的,女子子适人者为父服不杖期,父亲则为之服大功,两者不对等,故而不是报服。所以说,庾氏的论证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厌降唯子而已”的判断,以及“既出无厌”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22] 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第467页。
[23] 郑玄在论述“降有四品”时,云“为人后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则两者都是“出降”。“出降”父母的原因都是“不贰斩”,女子子是因由“从父”变为“从夫”而“移天”,为人后者是因“持重于大宗”,而以所后者为父,两者所尊之“天”皆非己父,似乎都应该解除厌降。
[24]丈夫与父亲爵尊之比较,仅影响父亲对己身的尊降,如大夫为女子子适士者,不但要出降一等,还要再尊降一等;但是女子的厌降是肯定随着“移天”而解除,这与夫、父爵尊差异无关。
[25] 曹元弼,《礼经校释》卷一六,第438页。
[26] 杜佑:《通典》,第2229页。
[27] 晋代的反向为后非常多,如晋元帝为琅邪恭王司马觐之子,登帝位之后,以其子裒奉觐之祀。又因东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元帝又以其子冲,出后毗,称东海世子。这些都是反向为后的例子。
[28]《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版,第1130页。
[29] 晋代诸侯王、大夫已经没有了尊降、厌降,如徐邈云:“汉魏以来,王侯皆不臣其父兄,则事异于周,故厌降之节,与周不同。缌犹不降,况其亲乎!既不以贵降,则余尊之厌,故五服内外,通如周之士礼,而三降之典不行同矣。昔魏武在汉朝,为诸侯制,而竟不立。荀公定新礼,亦欲令王公五等皆旁亲絶周。而挚仲理驳以为今诸侯与古异,遂不施行。此则是近代成轨也。《记》又云‘古者不降’,故孟武、孟皮得全齐缞。然则殷周立制,已自不同,所谓质文异宜,不相袭礼。大晋世所行,远同斯义。孔彭祖昔咨简文帝诸王所服,圣旨以为近代以来,无复相降。”(见杜佑:《通典》,第2531页)但天子应当还有尊厌降。
[30] 当然,齐衰三年和大功的提法,实际上有深层次的用意,详见下文分析。
[31] “疑”字,点校本《通典》属上句,作“经文则一,而郑有二疑”。但郑玄并非是怀疑《丧服经》的内容,而是进行了解释,认为公之庶昆弟为母大功是属于余尊厌,故而云“君卒”,大夫庶子为母大功是厌降,故而强调父卒之后解除厌降。这两点都不是疑问,所以“疑”字当属下句。
[32] “本亲祖父母、伯叔”点校本《通典》作“本亲、祖父母、伯叔”。此处讲的是为人后者出降本宗亲属,则“本亲”应该是形容词,修饰之后的“祖父母、伯叔”,故不应点断。
[33] 杜佑:《通典》,第2229页。
[34] 杜佑:《通典》,第2229页。
[35] 杜佑:《通典》,第2230页。
[36] 张锡恭:《丧服郑氏学》,第895页。
[37] “况于太宰贵,同古例不为父后者耶?”点校本《通典》作“况于太宰,贵同古例,不为父后者耶!”。前文崧重认为,母以子贵,庶子为父后者能够尊崇其母,由缌麻加至齐衰三年,“不行妾母之制”。而庶子不为父后者,则受到余尊厌,为母仅服大功,即行“妾母之制”。太宰尊贵,虽然不是为父后者,也应该取法母以子贵,为母齐衰三年,而不是行“妾母之制”服母大功。那么太宰与“古例”中的“不为父后者”不同,所以改点校为“同古例不为父后者耶?”
[38]杜佑:《通典》,第2229-2230页。
[39] 因为《春秋》中“母以子贵”指的是庶子继承父亲君位之后,将生母追崇为夫人。但太宰是出后诸侯王,不为元帝之后,不为父后,则谈不上“母以子贵”。而崧重以为汉魏以来皇子都为始封君,太宰不出后就为始封君,可以适用“母以子贵”。但这个证明是苍白无力的,事实上,太宰就是出后,而没有成为始封君,两者性质不一样,不能以始封君的假设取代为后的事实。
[40] 杜佑:《通典》,第2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