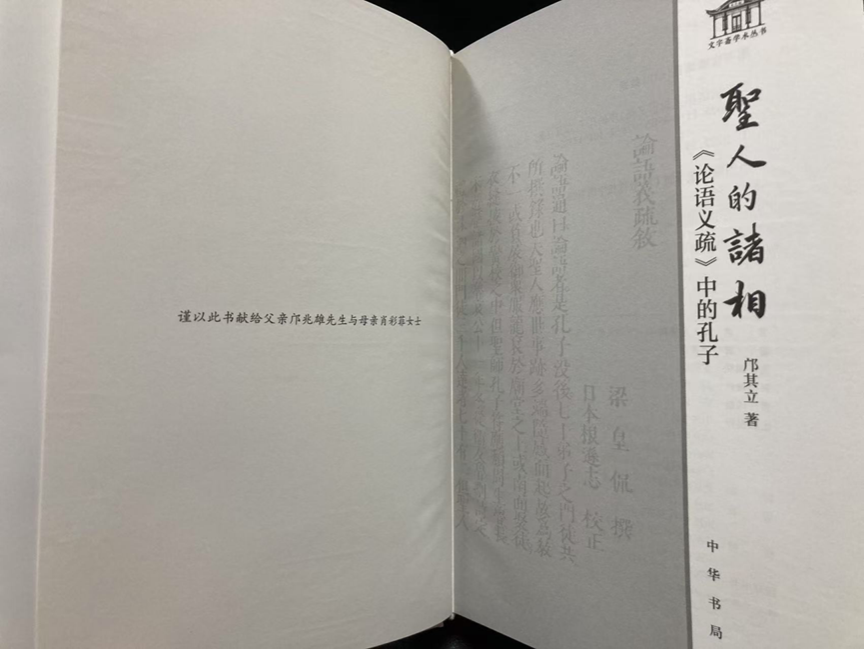【作者简介】
邝其立,哲学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儒家经典与解释,魏晋玄学。在《哲学研究》等核心期刊发文十余篇,主持并完成国社科青年项目一项。著有《圣人的诸相——〈论语义疏〉中的孔子》。
【内容介绍】
南朝梁经师皇侃奠基经学、综摄玄佛以重塑儒学。其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氏著《论语义疏》的圣人观中。透过这尊孔子形象,既能揭开六朝儒学的面貌,亦能管窥经学演进的逻辑。
【序言】
《论语》与圣人之教
陈壁生 | 序
在中国古籍中,《论语义疏》的地位非常特殊,在体例上,它是惟一一部保存全帙的六朝义疏学著作;在思想上,它是惟一一部完整的以玄言注《论语》的著作;从作者看,它是梁朝经学家皇侃惟一一部完整的存世之作。《论语义疏》最为集中地保存了汉晋六朝数百年间对《论语》的理解,要探求《论语》古义,舍此书则出不由户,行非斯道。
一
从《论语》解释史的角度看,《论语义疏》的思想非常特异。先来看一则注解,《为政》载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则语录,后世一般理解为孔子的夫子自道,但皇侃注解,甚有深意,其说云:
此章明孔子隐圣同凡,学有时节,自少迄老,皆所以劝物也。
孔子分明说“吾”,而皇侃却要说孔子是把自己当成凡人,来看凡人一生在不同年龄所能达到的不同境界。这是因为,在传统的理解中,圣由天纵,并非通过学习所得。孔子圣人,生而知之,不须志学方能有立。并且,如不惑、知天命、耳顺等,只是凡人学问进境,不可视为圣人一生的不同阶段。那么,孔子如此说法,必然有其深意。在皇侃看来,深意即是孔子“隐圣同凡”,把自己当成凡人来描述不同生命阶段所应该达到的境界。
“隐圣同凡”意味着在皇侃的理解中,圣凡悬绝,凡不可能成圣。事实上,这正是宋代之前与之后的儒家思想在理解“圣人”问题上的根本区别。既然凡人不可能成圣,那么圣人便有其独异之处,惟圣能够知圣,后世之凡人,包括贤人,本不能知圣。也就是说,如果《论语》真的是孔子的言行实录,那么,《论语》对后世之人而言,本来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
《论语》的不可思议性,是理解《论语》最为根本的根基。
与《论语》不同,圣人所遗,有可以理解的东西,那是圣人故意让人能够理解的,即圣人留下的法度。在两汉二晋六朝隋唐学者看来,圣人留下的法度,主要在五经。西汉人普遍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汉制法”,其他的《诗经》、《尚书》、《仪礼》、《周易》,孔子或述尧舜三代之法,或赞伏羲文王之道,但这些孔子之前的经典,经过孔子的“折中”,共同构成了孔子的法度。而郑玄之后,在这些经典之外,又加上《周官》等古文经典,也都是古代圣王如尧、舜、周公的遗法。简言之,五经都是“圣人之法”。
而圣人制作法度,不是为了彰显圣性,并非空作,而是制作当朝之典宪,或后世之垂法。因此,不管是如《春秋》别嫌明微的缜密,还是如《周官》三百六十官的严整,抑或如《周易》卦爻的繁富,后人或以家法传微言,或据文字察大义,皆可以解此“圣人之法”。对后人而言,知圣人,与知圣人之法不同。圣人之法本来就是规范天下之道,后世天下合之则兴,违之则败,大凡拨乱反正、制礼作乐,都要穷究圣人制作之微意,才能施行于天下。
在汉代经学中,五经为“经”,《论语》《孝经》为“传”,这一理解结构,已经决定了汉代以《论语》、《孝经》通五经的基本思路。汉代经师普遍传习《论语》、《孝经》,故喜以五经注《论语》、《孝经》,最典型的是郑玄以《周礼》注《论语》,使《论语》中孔子的言辞,都有《周礼》的制度背景。这样,《论语》中的孔子之教,与《周礼》中的周公之教,获得了一致性。比如《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郑玄注“道之以德”便说:“六德,谓知、仁、圣、义、忠、和。”(宋翔凤辑,《论语郑注》)如果不知他经,这明显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注释。因为,《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德”,从无六德之说,更无把“圣”与其他五德如此并列之例。但是,郑玄之注却是来自《周礼》地官大司徒所职,其文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周礼注疏》)这样一来,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便不只是泛泛而言道德,而是具体以《周礼》中的六德来引导民人。在郑玄心目中,《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周公还政成王之后,得以施行于天下,孔子是周人,颂扬周礼,所以孔子教诲弟子,背后必然有《周礼》的背景,而“道之以德”,是周人之德,自然便是周公所制《周礼》中的“六德”。郑玄此注,便把《论语》放到了《周礼》的制度之中,简言之,汉唐之间几乎所有的经师在注解《论语》的时候,都必然考虑《论语》与五经的关系,要不考虑其同,要不凸显其异,专言其同者,最典型的是郑玄的《论语注》,专言其异者,则自何晏《论语集解》始。
将《论语》从五经中独立出来,视为不同性质的经典进行注解,就目前来看,比较确定的是从何晏著《论语集注》开始。事实上,王弼、何晏倡为玄言,天下纷然讲“圣人体无”,辨圣人有情无情之后,《论语》作为记录“圣人”本身的经典,才与作为“圣人之法”的五经有分离的可能。但是,这种分离并不意味着《论语》与五经没有关系,而只是对其关系进行新的安排,即不能径直以五经为基础来理解《论语》,否则,五经与《论语》便成为同一性质的文献。但二者无论是从作者、内容、形式等方面看,都分明并非同一性质的文献。从王弼、何晏受到《老子》的刺激,开始思考“圣人”本身,《论语》的性质才得以开始真正讨论,圣人制法与圣人本身,并非同一“物”。到了皇侃要为《论语》作疏的时候,天下流行的注本主要有何晏注、郑玄注二本,而皇侃本来最擅郑学,其《礼记义疏》、《孝经义疏》,都是疏解郑注,独《论语》,专舍郑玄,而独用何晏。这可以见到皇侃自己独到的眼力。因此,要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第一步就必须理解“舍郑用何”的原因所在,非此则不能解皇疏。邝其立的《圣人的诸相》一开始就注意到《论语》独立化的问题,是本书非常重要的创见。
二
将孔子从五经中独立出来,并从孔子来重新理解《论语》,首开其端者是王弼。据何劭《王弼传》,王弼十几岁的时候见裴徽,有一段对话:
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三国志》)南朝宋齐时期,周顒答张长史书,犹云:“王、何旧说,皆云老不及圣。”(《宋思溪藏本弘明集》(二))王弼在这里表现出极为高妙的智慧,因为在汉代经学中,孔子制作六经,六经中多是修己治人之道,不讲魏晋时据老子提出的对世界本源的理解,即“无”。那么,是否孔子没有理解到本源问题,反而是老子深入其中?王弼在这里提了一个绝妙的回答:孔子早已以无为体,但无是无法谈论的,所以不说无,只说有。相反,老子并没有体验到无,所以申说不已。就此可见,不说无的孔子比说无的老子更加高明。王弼既保存了五经的地位,又在五经之上加进了道家,既提高了老子的地位,又把孔子放到老子之上。
在这里,无是“万物之资”,即本源,或孔子“体无”,都不是儒家之学,而是老子之说。但王弼这一安排的重要性,是使孔子从五经(“有”)中脱离出来,使不用五经来理解孔子成为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在王弼、何晏之前,对圣人,只有《周易》中的“与天地合其德”,《春秋》中的“素王”等非常粗线条的描述。但是,王弼、何晏之后,开始有“圣人体无”、“圣人无情”等各种接近圣人的理论命题。也就是说,对圣人问题的讨论,由隐而显,自粗而精。而且,因为魏晋六朝人重“情”,使这一时期对于圣人的认识,虽有凌虚空凿之弊,但毕竟高蹈远廓。无论如何,高蹈远廓要比亲切感人更加深刻。
至此,才能理解《论语》的重要性。在群籍之中,涉及到圣人的,屈指可数。五经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五经所载,都是圣人之法。《尚书》中的《尧典》是尧舜之法,《禹贡》是禹之法,《诗经》中的《商颂》是殷商之法,《周颂》、大小《雅》是文王、武王之法,《周礼》是周公之法,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其人,隐藏在法度的背后,并无直接的显现。即如孔子制作《春秋》,背后是笔削褒贬的“素王”,由《春秋》也看不到作为圣人的孔子本身。幸有孔门弟子,随侍夫子,圣人在世之时,于其言行动作,随时笔录,夫子徂背,又集而论纂,以为《论语》二十篇。由此,《论语》的特殊性在于,这本书是圣人在世之时的言、行实录,也是自伏羲尧舜至于周公孔子,惟一记录圣人本身的作品。简单来说,后世在五经甚至《孝经》中,看到的都是圣人为人世间安排的生活秩序和道理,而通过《论语》,终于看到了圣人本身的样子。而且更重要的是,只有《论语》,才让后世看到了在世圣人。因此,研究《论语》,不是要研究《论语》中的道理,而是要通过《论语》来看孔子作为圣人的样子。在中国经学史上,注解一部经书,不是为了经书中的道理,而是为了经书中的人,《论语义疏》可以说是惟一一部。邝其立的《圣人的诸相》一书把主题放在“圣人”之“相”上,而不是放在皇侃的思想,或玄学的特征,或六朝的儒学,是对《论语义疏》非常准确的定位。
《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夫子言行实录。现存最早讲到《论语》的是班固《汉书》的《艺文志》,其实来自刘歆的《七略》,其中说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论语》有三类内容,一是孔子应答弟子,二是孔子应答时人,三是弟子之言但被孔子听到。这里非常关键的是第三点,因为光从文本读《论语》,其中不但有孔子的言辞行事,而且还有弟子的语录,如《学而》开篇便有子夏曰“贤贤易色”,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些内容到底是算“孔子的思想”,还是“子夏、曾子的思想”,现代读者注重“著作权”,便以为并非夫子之语,不算孔子思想。事实上,古代注家如朱子,也会对《论语》中非孔子之语看低一头,觉得只是贤人之言而非圣人之言。但《艺文志》特别强调“接闻于夫子之语”,意思是说,这些话虽然并非孔子所说,但都经过孔子认可,同样应该看成孔子的思想。皇侃继承了《艺文志》的这一看法,在《学而》第一章“子曰”下说道:“此一书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时俗之语,虽非悉孔子之语,而当时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预录。”皇侃特别要加上这一说明,是因为在他看来,《论语》是弟子在孔子去世之后,为了留下圣师往训,从而撰作此书,没有理由把其中一部分内容看成无关孔子的弟子思想。
为何要特别说明《论语》每一则内容与孔子的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在皇侃看来,《论语》是一部通过孔门弟子的视角展现孔子本人的书,而孔子是圣人,所以,《论语》是展现在世圣人之书。在《论语》的每一则内容背后,都站着一个记录者,这个记录者同时也记下了有若、子夏、曾参等弟子的语录,这些被记下来的内容,都是在孔子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论语》作为一本独立于五经的书,系统地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生活。
后世读《论语》,绝大多数是通过《论语》读孔子的思想,关注的对象是思想,不是孔子。但皇侃的《论语义疏》关注的对象重心首先不是思想,而是孔子本身,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关注思想,就要对《论语》中的思想观念进行系统化的解释,非思想观念的行为也要进行思想观念化的理解,所关心的问题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话语、行动的意义。而关注孔子本身,则是从作为圣人的孔子的角度,讨论夫子为何要如此说话、行事。比如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以求之者也。”皇侃解释道:“知之,谓知事理也。孔子谦以同物,故曰我有所知,非生而自然知之者也。王藻云:‘此盖自同常教,以身率物者也。’”(王藻”,整理本误为“《玉藻》”。)孔子本为生知的圣人,但《论语》竟录他说自己并非生知,而是学知,皇侃的理解的方向,不是解释孔子之意,而是孔子为何这么说,即孔子谦虚,显得与凡人相同。又引用王藻之说,进一步解释孔子这么说的原因,是把自己放到凡人的位置上,才能以身教凡人。又如“颜渊死,子哭之恸。”皇侃解释道:“恸,谓哀甚也。既如丧己,所以恸也。郭象云:‘人哭亦哭,人恸亦恸,盖无情者与物化也。’缪协曰:‘圣人体无哀乐,而能以哀乐为体,不失过也。’”颜渊死,孔子哭得脸上无意识地变形了,这是描述孔子的哀痛。但孔子是一个活着的圣人,皇侃引用郭象之言,以圣人无情,所以孔子的“哭”和“恸”,是圣人把自己看成凡人,像凡人一样表现情感。
皇疏对《论语》的这种理解方式,按照邝其立的说法,都是属于“玄学化的圣人”。即先有玄学理论,再来看孔子的结果。
三
在《圣人的诸相》中,邝其立还着重讨论了《论语义疏》中的“教”,尤其是分出“言教”与“政教”,来理解皇侃眼中的孔子之教。事实上,“教”确实是皇侃理解《论语》的基本方式。但是,把《论语》理解为孔子之教,有多种方式,皇侃恰恰是采取了最独特的那一种。
通过《论语》理解孔子之教的内容,理解孔子的思想,朱子的《论语集注》把这种读书法发挥到极致。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有“读论语孟子法”,朱子引用程子之言曰:“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四书章句集注》)与此前不同,程子之后的理学,在读经上有一个基本预设,即“圣人可学而至”,因此,读《论语》中的圣人之言,要通过各种自修之法,理解“圣人之意”,圣人之意其实就是思想。朱子又引程子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若能于《语》、《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四书章句集注》)要理解圣人之意,在读《论语》上最深的读法,是通过文字,把自己融入到《论语》的情景中,扮演孔子的弟子提问,使孔子的回答如亲闻夫子之教,深求玩味,有悟于圣人之道,涵养自身气质。程子的这种读书法,在朱子《论语集注》中得到了深入的贯彻。朱子的《语类》也记载他所说的:“孔门问答,曾子闻得底话,颜子未必与闻;颜子闻得底话,子贡未必与闻。今却合在《论语》一书,后世学者岂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朱子语类》)朱子此语在程子基础上更进一步,以为《论语》一书中,孔门每个弟子只能得其部分,而后世学者却能得其整全。在这里推出了一个非常强的观点,即千载之后的学者因为得《论语》之全,甚至可以比孔门弟子更加理解孔子。在《论语集注》中,朱子的许多注解方式,包括注意《论语》语录的言说者,并对孔门弟子之言有所臧否,包括断言弟子没有真正领会孔子之意,等等,只有在朱子这种读书法中,才可能得到理解。简言之,朱子的读《论语》法,决定了朱子理解中的圣人之教,是孔子向弟子,也向万世读书人教诲道理。这些道理,类似于今人所说的《论语》中的思想。
皇侃的理解的独特性,在于认为《论语》中的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就是“教”本身。在《论语义疏》序言中,皇侃一开始就表明,《论语》是孔子之教,他说:“夫圣人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又说:“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应机作教”,是皇侃理解《论语》中孔子之教的方式,而具体表现,皇侃一口气列了四种,每一种都对应于具体内容,富含深意。
皇侃读《论语》的独特方式在于,他把《论语》每一章都理解为孔子教化的行动。不论是只有“子曰”开头的语录,还是具有情景的对话,或者是记述孔子的行迹,首先是圣人的教化,其次才是作为教化内容的思想。
空言难解,实例可证。上文所引《为政》中,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句,并无情景,也无对话,完全是夫子自道。如果纯粹从思想的角度,可以探讨十五、三十、四十到七十不同年龄阶段,之所以志学、立、不惑、耳顺。如果增加教化的视角,可以讨论孔子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境界,来看圣人是如何实现不同阶段的自我超越。但在皇侃的理解中,这一章的重点,不是其内容,而是孔子在说。所以皇侃一开始便解释道:“此章明孔子隐圣同凡,学有时节,自少迄老,皆所以劝物也。”孔子隐藏自己圣人的身份,把自己等同于凡人,教诲凡人一生不同阶段相对应的行动和境界。所谓“圣人之教”,不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而是孔子说出这句话,便已经是在进行教化。
《论语·子罕》有一则有情景的内容:“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皇侃解释道:“心服曰畏。匡,宋地名也。于时匡人误以兵围孔子,故孔子同物畏之。”又引孙绰云:“夫体神知几,玄定安危者,虽兵围百重,安若太山,岂有畏哉?虽然,兵事阻险,常情所畏,圣人无心,故即以物畏为畏也。”圣人体神知几,本来不应有“畏”,但是,圣人之外的凡人,面对凶险局面,都应该有“畏”,因此,孔子“同物畏之”,“以物畏为畏”。孔子一方面表现出“畏”,一方面又言“匡人其如予何”,本来深不可解,皇疏从教化角度出发,认为孔子所说,是隐圣同凡,使人知有所畏,而后又言自己是继文王之文,匡人不能违天害己。在这种理解中,重点不仅是孔子的“文不在兹乎”,而且更在孔子既“畏”又说,本身便是以凡人之情为己情,由此彰显圣人在世的真实生命。
在皇侃的解读中,每一句话都是孔子教化的行动,由此不惜把《论语》寓言化。例如《论语 》云:“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这句话在解释史上聚讼纷纷,皇侃引珊琳公曰:“宰予见时后学之徒将有懈废之心生,故假昼寝以发夫子切磋之教,所谓互为影响者也。”又引范宁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岂不免乎昼寝之咎以贻朽粪之讥乎?时无师徒共明劝诱之教,故托夫弊迹以为发起也。”释慧琳认为宰我是“假昼寝”,范宁认为是“托夫弊迹”,指向的都是共同的意思,即宰我并非真的像孔子所说那样朽木不可雕,而是假借当时之弊,来引诱孔子申发教化之言,而孔子也遂其所欲,批评宰我。在这样的解读中,昼寝并非真昼寝,诛责也非真诛责,都是为了教化时弊。又有“宰我问三年之丧”章,宰我主张为父母服丧一年,并且说一年即已心安,孔子直斥其“不仁”。皇疏引缪播说:“尔时礼坏乐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惧其往,以为圣人无微旨以戒将来,故假时人之谓,咎愤于夫子,义在屈己以明道也。”又引李充曰:“孔子目四科,则宰我冠言语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发违情犯礼之问乎?将以丧礼渐衰,孝道弥薄,故起斯问以发其责,则所益者弘多也。”一般的注解,都是论证三年之丧的合理性,但皇疏不但论述合理性,而且认为这段对话,实质上是宰我牺牲自己,装作时人,引导孔子进行教诲,从而使将来之人皆明三年之丧。
作为惟一一本展示在世圣人的生命与生活的作品,《论语》本来是不可解读的。圣凡悬绝,凡人可以通过学习而为贤人,而不可能为圣人。但《论语》又是可解的,如果考虑到《论语》中绝大多数的孔子之言,都是对弟子而言,即便以“子曰”开头的纯粹孔子之言,背后也站着一个作为弟子的记录者,这个弟子的存在,也使孔子之言是对凡人所说,因此,《论语》的可解,便在于每一则内容都是圣人对凡人所说之语,弟子、时人作为凡人,可以通过语言知圣人之意,后世凡人也可以通过文字知圣人之意。正因如此,对《论语》的解读,只能站在凡人的角度,以凡人之眼观圣人言行,这样,圣人的言行,都只能是教化。当玄学兴起之后,开始讨论孔子作为圣人的圣性,便必然要把《论语》理解为一本教化之书,即展示圣人如何行教。
在皇侃的解读中,《论语》的每一句话,首先是教化,然后才是思想。也就是说,当孔子说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时,便已经是在进行一种教化的行动。后世注家关心“学”、“习”、“说”之义,并讨论其关联,这是理解这句话的“思想”。而在皇侃看来,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必须将这句话理解为夫子的教化行动,由教化行动去理解圣人本身。从这一读书法出发,看到的首先是孔子,其次才是孔子之言,首先是圣人,其次才是圣人的思想。在《论语》皇疏中,活着一个正在教诲弟子时人的圣人。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够去理解《论语》中许多看起来比黑格尔所说的“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哲学史讲演录》)更为无趣的内容的意义。在《论语》中,一些内容看不出“思想”,例如别人向微生高借醋,微生高向邻居要了借给人家,孔子说这不是“直”,例如孔子弟子观察到的,孔子当天参加吊丧,就不唱歌,等等。从皇侃式的教化的角度看,这些内容,与“慎终追远”、“非礼勿视”之类同样重要,因为都是表现了一个在世圣人鲜活的生命。孔子在进行教化的时候,不是通过讲道理去说服读者,而是通过他的言辞与行动,直接展现道理本身,使读者在《论语》的各种细微的辨析中,直接去接近圣人。皇侃揭示了一种早已湮没的古典教化之道。
四
在《论语》解释史上,皇侃的《论语义疏》是一本绕不过的著作,但相关的研究,与本书的重要性程度很不匹配。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现代哲学研究中,对魏晋六朝哲学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这与这段时期的思想构成比较复杂有关。皇侃的《论语义疏》所据的注本是何晏《论语集解》,本来就集七家注解,加上何晏自己共八家。而皇疏由据晋朝兖州别驾江熙所作的《集解论语》十卷,江熙所集晋朝共十三家。皇侃所作《义疏》,除了偶尔两存其说,大多数注解都有较好的裁断。但毕竟所集多家,且晋朝十三家作注之时,正是道家、佛教与经学大融合的时代,皇侃自身又受到佛学影响,这都导致《论语义疏》的思想成分非常复杂丰富,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邝其立从陈少明老师治《论语》,他的《圣人的诸相:<论语义疏>中的孔子》勇于挑战,直接把《论语》皇疏的主题定位在“圣人”问题上,本身便非常正确,且需要学力与眼光。书中对儒玄交涉、圣人教化等问题,都有非常深入的揭示。事实上,研究《论语义疏》,最难的是在大方向上把握皇侃的思想,并以此通达对《论语》的理解,邝其立的著作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圣师:《论语》的独立化与孔子教化形象的凸显
2.1 《论语》独立化的历程
2.2 《论语》独立化的背景及成因分析
2.2.1 经学史的脉络
2.2.2 思想史的脉络
2.2.3 方法论的因素
2.3教化形象的树立
2.3.1 “作教”
2.3.2 “应机”
第三章 玄学化的圣人
3.1 孔子的本与迹
3.1.1 融通诸教
3.1.2 “圣人体无”
3.2 作为方法的言意之辨及其意义
3.3 言意与本迹:皇疏的“复合结构”
第四章 涉玄的意义
4.1 “体无”或“教化”:论皇侃圣人观的核心
4.2 “体无”与“同天”:对孔子的两种说明
4.2.1 对圣人身位的新证明
4.2.2 儒、道圣人观之交集:“因循为用”
4.3 涉玄之于儒学转型的意义
第五章 言教与政教:皇侃对教化的两种理解
5.1 言教:“隐圣同凡”
5.2 言教的展开:“圣贤相予”
5.3 政教:礼乐之风化
5.3.1 礼教
5.3.2 乐教
5.3.3 风草之喻
第六章 圣王:孔子的政教之心
6.1 先王之道
6.1.1 论“学”
6.1.2 五经的意义
6.2 《论语》与五经——从管仲形象说起
6.3孔子的另一面
6.3.1 圣人“知时”
6.3.2 “同于尧舜”
6.4孔子形象与六朝学人的精神世界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