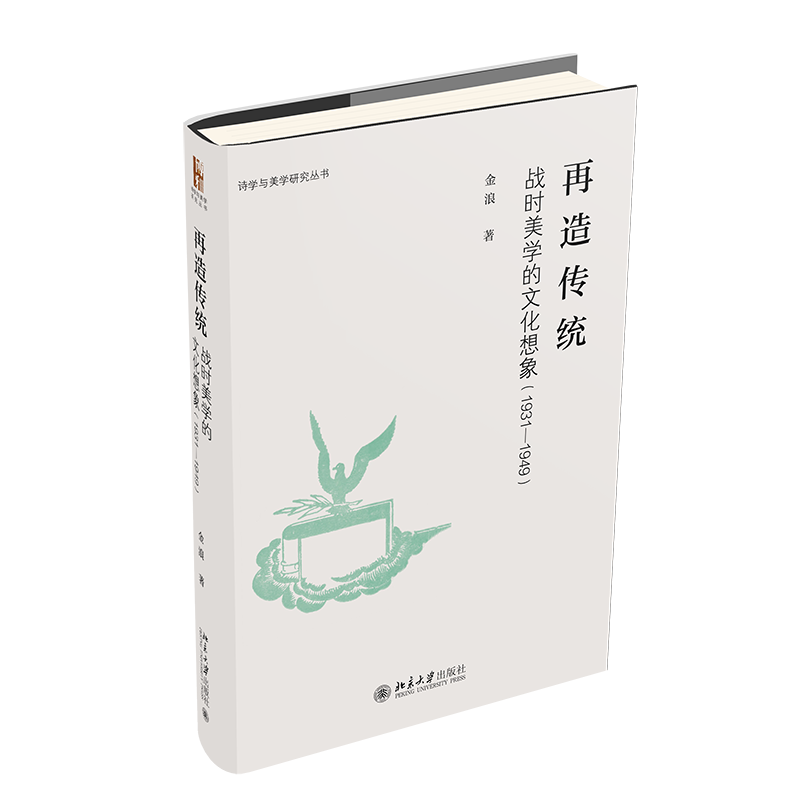
书名:《再造传统: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1931-1949)》
作者:金浪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9月

【作者简介】
金浪,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雅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青年分会学术委员等,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现当代美学、文论与文艺批评,著有《理论的边际: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美学探思》。
【内容简介】
无论就哪方面而言,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在战争状态下的新发展,都理应受到足够重视,它不仅极大改变了美学话语在现代中国的面貌,使之从言必称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尼采,转向了儒家、道家、禅宗、心性、礼乐、意境等更能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术语,实现了“美学的中国化”,同时也经此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将审美和艺术精神打造为中国文化特质,从而促成了“中国的美学化”,更重要的是,后来经由人民性的洗礼,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对“中国美学”知识范式的当代涌现更是产生了不可估量之影响,甚至潜移默化地参与了新时期“美学热”的开展。
本书围绕文化想象的主线重启对战时美学的研究,力图突破新启蒙主义的思想框架,正视战争状态下中国现代美学的新发展及其经由美学再造传统之努力。通过对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三位代表性个案的分析,本书不仅旨在勾勒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在三人论著中的具体开展,更力图呈现其中的丰富性、复杂性及其所遭遇的难度与困境。
【全书目录】
绪 论/ 001
一、“美学”与“中国”的磨合:知识范式的现代生成/ 002
二、文明与文化的纠葛: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美学/ 008
三、经由“美学”重返“中国”:文化对流中的未尽命题/ 015
四、“再造传统”的美学路径:战火中的文艺复兴构想/ 024
第一章 美学视野下的儒学“转向”——朱光潜论/ 035
第一节 从中国“诗”到“中国”诗:《诗论》的美学转进/ 036
第二节 “以情释儒”:从《陶渊明》看儒家美学的理想形态/ 056
第三节 处群追问下的共通感重构:修养与美育之“互通”/ 072
第四节 重估“儒家审美主义”:儒家礼乐精神的美学重释/ 089
本章小结/ 106
第二章 创构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宗白华论/ 108
第一节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从动静文明论到文化形上学/ 110
第二节 “写实”挑战下的艺境创构:从与徐悲鸿的对照视野看/ 125
第三节 以“艺术”重构“中国”:中国文化精神缘何“美丽”/ 144
第四节 历史断裂处的魏晋想象:“晋人之美”如何浴火重生/ 161
本章小结/ 179
第三章 古典与浪漫之间的文艺复兴——李长之论/ 181
第一节 以“批评精神”烛照传统:文艺复兴的方法论自觉 / 182
第二节 通往古典精神的文艺复兴:从“五四”运动再出发 / 200
第三节 古典、浪漫与写实:古代诗人批评的美学构造及运作 / 215
第四节 从“壮美”拯救文人画:中国画论批评的美学策略 / 234
本章小结 / 251
结 语/ 254
参考文献/ 260
后 记/ 268

【选摘】节选自全书绪论第一部分
“美学”与“中国”的磨合:知识范式的现代生成
本书关注的是“中国美学”知识范式在战争时期的话语生产,所谓“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便是对这一话语生产机制的描述。虽然“中国美学”在今天已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学科领域,不仅每年都有大量冠名“中国美学”的著作和论文面世,召开各种有关“中国美学”的学术会议,“中国美学”也为国际美学界所接纳,中外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交流与对话,使得“中国美学”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中国美学”取得的这种成就,固然令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深感自豪,但据此认为“中国美学”乃中国固有之概念,甚至将之目为“国粹”,则不免让人生疑。“中国美学”,不仅孔子、刘勰闻所未闻,恐怕连严羽、金圣叹也会一头雾水吧。从概念史的角度而言,“中国美学”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概念。虽然美学早在清末民初便经由日本传入,并在民国时期影响甚巨,但彼时“中国美学”的提法并不常见。哪怕是后来被推崇为“中国美学”大师的宗白华,尽管其对“中国美学”影响深远的论著大都完成于民国时期,但征诸其全集不难发现,他在民国时期很少采用过“中国美学”这一概念,而更多的是代之以“中国艺术精神”“中国艺术意境”“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之类说法,迟至1960年代,“中国美学”的提法才大量现身于宗白华笔端。
正如宗白华的例子所呈现的,“中国美学”概念的频繁出现是美学大讨论之后的事情,其正式登场与一次国家统编教材有关。1962年,周扬主持全国文科教材编写,计划编写三本美学方面的教材,分别是由王朝闻负责的《美学概论》、朱光潜负责的《西方美学史》和宗白华负责的《中国美学史》,这也标志着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在历史书写上分庭抗礼之势的形成。虽然由宗白华负责的《中国美学史》最终未能完成,但他196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美学课程,已然在进行酝酿工作,不仅写下了不少的笔记,也为后来“中国美学”的开展培养了人才。正是在宗白华指导下,北京大学美学教研室的两位年轻人叶朗、于民合作完成了《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下)。作为写作美学史的资料准备,该著作1963年完成初稿,但直到1980年才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紧随其后,中国美学史的出版迎来了井喷期,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刘纲纪与李泽厚合著《中国美学史》(第一卷,1984;第二卷,1987)、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1984)、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1987)等书相继出版,将“中国美学”研究推向了高潮。
如果说“中国美学”概念在1960年代的出现,隐然传达出中苏论战背景下中国与西方(也包括苏联)分庭抗礼的政治自信的话,那么,这一概念在新时期以后的蓬勃发展,则转而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目标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如何实现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化,渐趋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议题。作为这方面的代表,曾师从宗白华并以研治“中国美学”著称的学者叶朗,便明确反对谈“现代美学”言必称西方的做法,不仅认为“西方知识界对于中国美学的这种隔膜与无知,是美学这门学科始终未能突破西方文化的局限的一个重要原因”[1],更进而发出了推进中国传统美学现代化的急切呼吁:
更值得我们严重关切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中国传统美学也了解得很少。学术界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我们已经发现很多很有意思、很有特色的东西,但是还来不及做深入的研究。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被掩盖了,被遗忘了,还有待于进一步发现。对于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精神和理论内核,我们还缺乏认识,至少还没有准确地把握。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我们应该下大力量发掘、整理、研究中国传统美学,用现代眼光加以阐释,并且努力把它推向世界,使它和西方美学的优秀成果融合起来,实现新的理论创造。这是我们中国学者对于人类文化的一个应有的贡献。[2]
这段发表于1994年的言论透露了作者彼时关于“中国美学”研究的宏大抱负,即以中国传统美学为根基,通过努力推动其现代化,使之贡献于人类文化,其责任感与使命感,今天读来仍令人肃然起敬。然而,一旦脱离了本民族文化的朴素情感及推动其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语境,同样是对于中国传统艺美学和艺术精神的欣赏,也许会就偏向不同的方向。在此方面,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朱利安(又译于连)颇具代表性。2010年,朱利安出版了《美,这奇特的理念》一书,六年后中译本出版。在该书中,朱利安通过考察美之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发生及演变,提出了美的观念是西方形而上学枢轴的看法,“‘美’命名这个存有的、显现的、超验性的以及感觉直接性的联结-障碍点,使它成为欧洲思想的固定的神经痛点。它是在可见之网中捕捉到的绝对,不停地对我们讲述着形而上学,这个它的难解之谜和魅力的——唯一的——力量来源”[3],并认为这与中国建立在关系性思维基础上的艺术理解完全不同。由此朱利安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人和日本人从西方借入美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中国人或者日本人从此像欧洲人一样使用这个美的范畴,而不再进一步向其主体提出质询,在这个美的范畴之下轻松地列入他们的“美学的”(esthétique)经验,后者被译为“美”的“学习”。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接下来不停地——正好在反面——想要阐述什么是他们的传统“美学”的渊源。……如此,美将他们与自身的过去相分离,而非更清楚地加以了解;与其说它有助于文化间的交流,它更将他们的艺术实践退回到无法描述之中,并且制造出分享的屏障。[4]
显然,朱利安并不具备叶朗那样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美学现代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恰恰相反,他延续的是其一贯“经由”中国(他者)反思西方(自我)的思路,故而,坚持认为中国文化独特的艺术思维应当尽可能避免美学这一源自西方的艺术思维污染,甚至批评以王国维为起点的中国现代美学已然误入歧途。即便后者用以修补西方美学的不足而提出的“古雅”范畴,也被认为是一种失败了的抵抗尝试,“它恰好地与‘共同的经验’(expérience commune)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以微妙却特征显著的方式如此制造着障碍的同时,在传统的外表和中国文人最平淡的修辞掩护下,像突然汹涌而至,并太令人不堪重负的伟大迷思,借入美。”[5]
由此可见,尽管同样对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论欣赏有加,但叶朗和朱利安的阐释方向可谓南辕北辙:前者立足于“中国”,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化,后者则将“美学”视作西方霸权,反对中国向西方“借入美”。二者孰是孰非并非此处重点,但这一鲜明差异已足以提示我们,“中国美学”中的“中国”与“美学”两个成分之间并非平滑顺接,而是存在着紧张甚至抵触。更重要的是,这一由叶朗和朱利安的阐释路径差异而得以呈现的紧张与抵触,不仅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中国美学”知识范式内部,也传递到了对美学家个案的研究上,比如近年来围绕王国维诗学究竟是以中学还是以西学为底色的问题,学术界便展开了激烈争论。罗钢一反过去认为王国维诗学属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现代转化的认识,力主其以德国美学为底色,并将之对中国古典诗学术语的运用称作“传统的幻象”,[6]而反对者则捍卫王国维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关联,批评罗著深陷后殖民主义泥淖。针对“中国美学”内部这场暗流汹涌的中西之争,汤拥华借助对宗白华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他力图跳出在“中国”和(西方的)“美学”之间各执一端的分歧,提出了将“中国美学”还原为现代知识建构的考察思路:
当我们讨论中国美学的现状与前景时,不需要反复争辩中国传统文艺思想是否具有当代意义和世界价值,而应问中国美学这个已经运作了近百年的范式是否仍有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又将从何处得到持续的补充。作为这一观念的调整,并不是要取消那些中与西的棘手争论,而是要将这种争论引向比较实在的争点。即便所有人都承认中国美学只是一种理论范式,也必须追问这种范式从何而来,其内在逻辑如何把握以及中西文艺思想资源与此范式的关系等等。一个尖锐的问题是:要使“中国美学”这一学术范式得以建立并具有现代价值,它究竟应该由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主导,还是由西方的美学逻辑主导?或许我们认为应该搁置这种非此即彼的抉择,代之以中西间富于建设性的对话。[7]
在汤拥华看来,与其纠缠于中国美学究竟是“中学”主导还是“西学”主导,不如转而追问美学在现代中国的特定境遇:“特定的研究者想让‘中国’还是‘西方’主导美学研究,可能不是第一位的问题,因为无论遵循哪一种思路进入,都要面对同样的难题。更值得我们去深入探究的,是美学这门学科在现代中国的特定境遇,或者说,是古今中西的复杂纠葛在美学这一学科领域展开时的特定样态。”[8]这是非常中肯的提醒。因为一旦“中国美学”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属于知识范式的现代建构的话,那么,问题的着眼点也就发生了转移。从知识范式的现代建构视野来看,“中国美学”既不是古已有之,也并非纯属舶来,而是“美学”与“中国”相互磨合下的产物。在这一相互磨合的过程中,中西美学资源发生着剧烈的碰撞与重组,其中不仅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人在审美领域会通中西的卓绝努力,也记录了他们立足美学实现文化主体性重建的艰难历程。本研究对“中国美学”知识范式生成的考察,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的。
前面已提到,“中国美学”概念的频繁出现,大致是在1960年代中苏论战背景下,而其大量成果的涌现,则更是晚至新时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中国美学”知识范式生成的考察,也必须从这一时间开始。对于概念生成的历史时段问题,从事概念史研究的学者方维规教授曾有所提醒。他指出,概念史研究的关注点不能纯以概念出现的数量为依据,“殊不知一个概念或关键词的重要性活关键发展,常常不在于频繁使用,而是取决于被论辩、被争夺的强度,或在某个历史时期和关键时刻的多义性和争议性及影响力,或在观察和解释社会、政治状况时的不可或缺。当这个概念已经‘家喻户晓’,人云亦云,也就是达到走势图中的峰值时,只能表明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却很可能已经失去锐气,无须多加思索,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失去对概念史有用的认识价值。概念史关注的是一个(重要)概念的生成、常态或者非连续性、断裂和变化,关注变化的转折点、衔接点、关节点,而这些都是计量分析无法胜任的。”[9]尽管本书无意于采取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但这一来自概念史研究的真知灼见却相当关键。因为它无异于提醒我们,要探究“中国美学”知识范式的生成及其背后的思想能量,必须从更早的时期入手。而本书之所以将“中国美学”知识范式的生成视作“美学”与“中国”相互磨合下的产物,同样意在说明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时段。相信这也是汤拥华将“中国美学”描述为“运作了近百年范式”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自作为现代学科话语的“美学”从西方(或经日本)舶来中国,“美学”与“中国”的磨合就从未停歇:一方面,美学因其作为普世价值的承载而被认为是社会改造的绝佳手段,美育面相由此得到凸显;另一方面,随着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走强,美学又被运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重构,而尤为复杂的是,在“美学”与“中国”的磨合中,社会改造的面相与文化建构的面相常常又是相互缠绕的。如果说社会改造的面相在“五四”时期占据了主导,那么,文化建构的面相则在抗战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正是在民族国家的危机中,“美学”与“中国”的磨合迎来了高潮时刻。抗战时期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与尝试,这些努力与尝试不仅丰富了战时传统文化复兴思潮的面貌,也提供了通往“中国美学”的多样路径。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现代知识范式的“中国美学”正是这些努力与尝试下的产物。因此,重返“美学”与“中国”磨合的高潮时刻,厘清其间的多样努力及其得失,不仅是有助于理解“中国美学”的话语生产机制,同时也是深入认识中国现代美学逻辑演进的关键线索。只不过,对“美学”与“中国”之磨合的考察并不能仅仅着眼于二者相遇的时刻,因为其思想资源早就深蕴于西方美学内部。
[1] 叶朗:《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国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3] [法]朱利安:《美,这奇特的理念》,高枫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
[6] 自2006年起,罗钢在《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清华大学学报》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十余篇讨论王国维诗学与美学的论文,持续阐发王国维诗学是以德国美学为底色的观点。2015年,这些论文被收录为专著《传统的幻象: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7] 汤拥华:《宗白华与“中国美学”的困境:一个反思性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9] 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