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1月17日下午,“弘道:重大哲学名家讲坛”第八讲暨重庆大学高研院文字斋讲座第146讲,在重庆大学A区声音图书馆成功举办。此次讲座主题为“《礼运》‘大同’何以是秩序探究的出发点而非目的地”,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主讲,重庆大学哲学系张文涛教授主持,重庆大学哲学系黄铭副教授与谈,数十名师生参与研讨。

“大同”“小康”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无论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建国之后,“大同”和“小康”都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政治话语和实践中,而《礼运》本身也从《礼记》当中逐渐升格独立出来。这一系列现象都与人们对现今秩序的深层理解密切相关。陈赟教授在本次讲座中对近代以来关于大同小康的主流理解提出了挑战和质疑。
陈赟教授首先梳理了传统上主要存在着三种去脉络化的“大同”解释取向:一是实体化的理解方式,这一理解通常将“大同”实体化为特定的秩序类型,例如以“德”为理念的“帝道”,或是秩序历史中的某一特定阶段;二是目的论或末世论的理解方式,将大同理解为秩序历史的终极完美形态,或是历史的彼岸性未来;三是乌托邦主义的理解方式,将其视为现实历史中无法实现的希望原理。将大同视为社会的至高甚至是终极理想,恰恰偏离了《礼运》的文本自身,是一种去文本化和去脉络化的实体性解读,而回归文本脉络可以生发对大同作为秩序经验的重新理解。
陈赟教授进而提出了自己对大同小康的另一种理解进路,即大同小康的叙事并非回归未见的“礼”字的“大同”,而是“礼之急”的感受,“大同”可以理解为一种原初性的秩序经验,在这种经验中,秩序无法剥离人的生存,且无法被人对象化地认识,它隐藏在一切秩序经验的背景深处,而《礼运》以“大道”“太一”“大同”等多种方式敞开了原初秩序经验的特征。
“大道之行”与“大道之隐”涉及了两种秩序经验,前者是自发性的没有秩序感的秩序体验,而后者则是被作为秩序的秩序体验,从“大道之行”到“大道之隐”,本质上是大道的自行分化。陈赟教授又从文本入手,讨论了这两种秩序经验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大道”作为道之本然,无所谓对谁显现的问题;“大道”在分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双重“显”“隐”问题、道的自行发用流行与人的关系问题。而古典中国思想中对“道”的刻画有多个层面,如大道、常道、可道之道、至道,通过对道的各种分殊形式的分析可以看出,一般而言,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形而上的“道体”是在工夫性的“体道”中显现的,这就避免了“道体”在非参与性语境中的的实体化取向。大道通过流行与分化的方式在人那里得以显现,人在“体道”体验中对之而有不同的敞开方式。《礼运》对“大同”的定位是既非某种秩序类型,也非某个秩序阶段,而是位于一切秩序类型和秩序阶段的经验背景深处并使得这种体验成为可能的条件。
从更根本层面上来说,原初秩序经验从本质上来说也就是原初宇宙经验,而“太一”这一概念恰恰就体现了原初秩序经验的宇宙论刻画。陈赟教授通过深入分析“太虚”“太极”“太一”等概念,梳理“太一”的特性、秩序经验的不同层次,即“太一”“太极”“太虚”“太初”“太始”为一层,天地、阴阳、四时、鬼神为一层,万物为一层,还原了中国古典语境中的原初宇宙秩序经验,又进一步解释了秩序经验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构建与传统解释进路所带来的困难。
总而言之,陈赟教授强调,在《礼运》中,“大同”必须与“大道”“太一”等关联起来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只有将大同理解为原初秩序经验,而不再是某种特定秩序类型或秩序历史的特定阶段,那么,大同作为秩序探究之出发点而非目的地,才能被真正阐明。这就意味着回到大同,或者以大同为终极秩序的构思,不再具有正当性。然而恰恰是这种对大同的构思,主导了对《礼运》的理解。而就《礼运》的整体脉络而言,不是回到大同和小康,而是走向“大顺”,才是其秩序之思的真正目的地。

在与谈环节,黄铭老师首先对陈赟教授对“大同”“小康””进行的概念式的翻案表达了认同,又进一步提到中国从宋代开始就有对大同小康的实体化倾向,而此倾向更是在康有为处被加深。康有为将大同小康实体化,在理解这一概念时更注重最高权力者的阶级问题,更是在大同小康当中引入了进化论的思想,因而得出了中国文化要向西方学习的结论。这种从大同小康中最终推出的结论是消灭政治和人伦,这一理解方式主导了现当代对大同小康的解读,也导致了我们在文本阅读的时候,难免会先入为主地代入此种理解思路。在以往实体化的解释思路下,大同小康通常会被严格区分为两个概念,但这种方式却无法对所有古典文本进行全面解读。也就导致了学界对一些大同小康的文献是否存在错简问题的争论。对大同小康之区分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若将前者视为有人伦而不自知的无意识状态,而后者为有人伦亦有意识,那么这两者中间的过渡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吴飞教授因此在这两个时代当中插入了“礼崩乐坏”作为过渡,圣人制礼作乐恰恰就反映了其重新构建秩序的努力。而陈赟教授的解读并没有局限于大同小康的区别,而是从更高的宇宙论视角来理解大同,与前一种解读中偏重“制作”不同,宇宙论下大道的自然分化也就意味着人为的制作不是必须。黄铭老师表示,陈赟教授对大道的解读方式对理解公羊学中的三世说与文质更替问题也有极大启发。陈赟教授对上述观点做出了相应回应。
其他在场的老师、同学也积极提问,参与讨论。本次学术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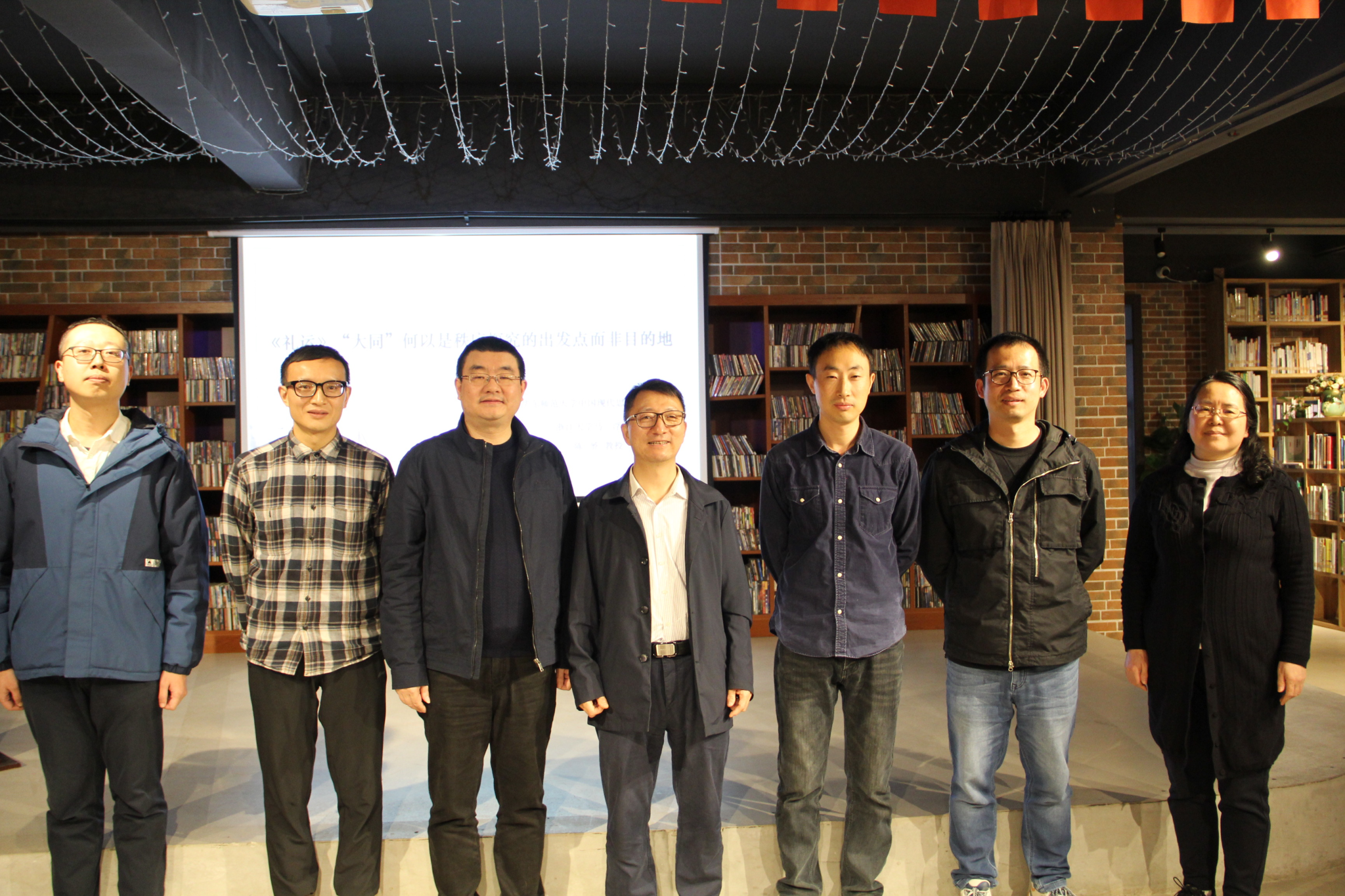
撰稿:颜子琦
摄影:潘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