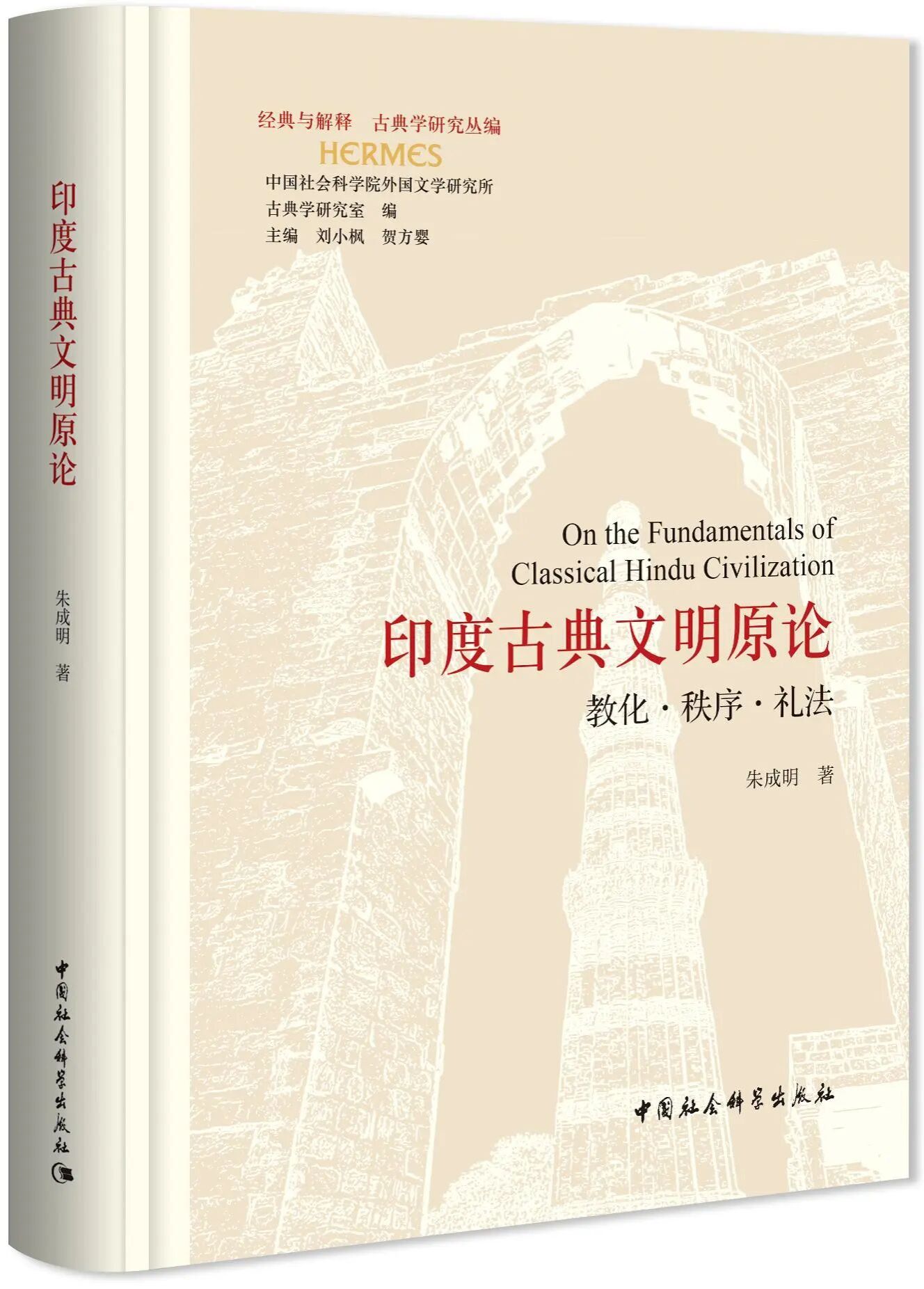
印度古典文明原论
——教化·秩序·礼法
朱成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8月
“经典与解释·古典学研究丛编”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古典学研究室 编
主编 刘小枫 贺方婴
印度教自称“永恒的法”或“吠陀法”,是南亚次大陆上大多数人数千年以来的生活方式,历久弥新。它渗透到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全面塑造了印度社会,构成一种无所不包的教化。对于古印度人来说,“法”并非单纯的法律,而是宇宙、社会、人生的正当秩序。具体到日常经验当中,则是政制性的法度或礼法。为了理解印度教文明的这个浓缩而丰富的内核,我们需要深入印度文明的根底处,从古印度知识传统出发,在古印度自身的精神、理智、文化语境中去观看“法”的阶段性形态(孕育、诞生、发展、定型),并廓清其在变迁过程中的意义和蕴含。本书将带领我们加入古印度先贤,去经历探究“法”和“正当秩序”的思想之旅。
前 言 /1
缩略语表 /1
第一章 探究正当秩序 /1
一 个人与社会的正当秩序 /2
二 作为秩序实质的灵魂秩序 / 8
三 如何探究古人的秩序构想? / 14
第二章 从印度到印度教 /21
一 “印度”之名 /24
二 “印度的”与“印度教的” /32
三 “印度教”与“婆罗门教” /39
第三章 古印度文明的奠基 ——吠陀与“如是说—古事纪” /47
一 吠陀本集 /50
二 梵书 /58
三 森林书与奥义书 /63
四 六吠陀支与法度经 /67
五 “如是说—古事纪”:《摩诃婆罗多》 /78
第四章 经验、实在、真理 /85
引子 阐释的难题 /86
一 回到常识,回到具体 /89
二 实在与真理;经验与经验模式 /92
三 对实在的言说与象征真理 /101
四 文本阐释的核心:回溯经验内容 /106
第五章 上古印度的经验、真理、智识史 /113
引子 “法立足于真” /114
一 satya[真]之三义 /116
二 上古印度:前科学真理及其效力 /122
三 上古印度的智识史分期 /126
第六章 古印度宇宙论神话真理与 ṛta[轨则] /133
一 吠陀前期的神话真理 /135
二 祭祀:宇宙之道和技术之道 /143
三 祭祀:阿耆尼及其真实 /147
四 satya[真实]与 ṛta[正当 / 轨则] /156
第七章 古印度 dharma 的脱胎与成型 /165
一 “法经之法”与“法论之法” /167
二 两种真理:求索“开端”和“彼所” /174
三 “开端”真理与 dharma 的脱胎 /182
四 梵书与 dharma 的成型 /190
五 吠陀中期 dharma 的特点 /195
第八章 作为正当秩序的 dharma /203
一 真理、法、立法者 /204
二 何为 dharma ? /212
三 人之目的:“三合一”与“四合一” /215
四 微妙难测的 dharma /220
五 dharma 意义的最终明晰 /224
六 dharma 建构的完成 /234
小 结 /241
参考文献 /243
后 记 /252
这是一本印度学(Indology)的书。按Indology的构词法,它指关于“印度”(India)或“印度事物”(things Indic)的logos,即关乎印度事物的“说法”“论证”“道理”“理论”。笔者盼望这本小书对相关印度事物的描述、呈现和分析,能尽量符合logos(这个词的古典哲学含义)这种特殊的言说和知识形式。
大概二十来年前,刘小枫、甘阳等老师开始在汉语学界倡导追溯西学源头,并大量引介西方古典文史的原典和研究著作。笔者彼时在修习印度学,但也比较关心西学古典,因此对刘、甘两位这种从文明、政制视角展开的古典学感到亲切。一直以来,笔者都通过出版物和这股学风保持接触,继续学习西方古典哲学,并开始格外留意关心“人类事务”的哲学。
在博士阶段,笔者的导师段晴教授把《利论》交给笔者,希望笔者就这部古印度治术典籍做一点初步研究。从这时候起,笔者开始关注印度古代政治秩序问题。很遗憾,直到毕业,笔者也没能把段老师期望的“《利论》研究”做出来。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笔者当时在政治学理论上缺乏严格的训练和装备,在某些核心学理问题上尚未得明晰,不敢贸然处理《利论》,遑论在更大语境中研讨古印度政治秩序的问题。
▲ 《利论》,憍底利耶 著,朱成明 译注
商务印书馆,2020年
对古印度政治秩序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国内虽然比较空白(到如今还是),但就着整个印度学界来说,当时其实已经有很多出版物可以参考。只不过,在笔者见识过古典哲人对“人类事务”秩序问题的处理之后,对现代“智识群体”(intelligentsia)的论说既不很信任,也实在提不起多大兴趣了。因为比较之下,二者在精神和理智身量上差距太大,反映到知识方式和知识品质,相别更不啻云泥。不过问题是,笔者当时虽仰慕古典政治哲学的知识方式,自己却无能力像古典哲人那样去处理相关问题。更直白地说,笔者当时的尴尬在于,虽然能识别那些大行其道但粗劣、业余的研究,那些不充分的知识方式,[1]却不能从结构层面明晰那类知识的内在缺陷,自己也不能相对充分地去处理——被那类知识方式所处理过的——相同或相似的问题。
在修业进程中,笔者越发感到,“哲学”“知识”“理论”这类词的意义在古、今各色人等那里有着太大差异。这里的“古人”与“今人”不指时间上的差别,而是心性、智识品质的区分。即便在当今这个世代,我们仍可以在智识场域(所谓“学术共同体”)中区分出诸多或古或今的心性、智识类型。
比如,有人生活在柏拉图学园(奥义书仙人—生徒圈子、佛陀的僧团亦同)式“自由教育”(ἡ ἐλεύθερα παιδεία)的氛围中;有人生活在中古的经院式、部派式学风中;有人生活在德国启蒙典范的“体系”(System)或“科学”(Wissenschaft)的光亮中;有人生活在英美经验—常识类型的“科学”传统中;有人生活在近世生存论“此在照管它自身”的“真理”中;有人生活在“××的终结”“××的死亡”这类“后现代理论”态势中;还有人——一方面尚未被后现代“先知”施洗,另一方面又无能追比近代以来的启蒙巨擘——生活在因多方稀释、一再分流而多得数不过来的各种意识形态(即形形色色的“主义”)立场中;当然,不用说还有人幸运地避开了一切劳神费力的长篇阅读、持续思考,满足地栖居在期刊报章这类“学术前沿阵地”上。
上面所列举的人一概叫“学者”,他们以知识生产为职事,他们也都使用“哲学”“科学”“理论”这类指称知识的词。唯一的问题是,随着使用者心性、智识品质的不同,这类词所蕴含的实底(substance)和成色大相径庭。[2]黑格尔可以说,他的志业是让哲学成为“科学体系”(das wissenschaftliche System),令哲学从“对知识的热爱”(die Liebe zum Wissen)成为“真正知识”(wirkliches Wissen),[3]不过这样一个宣告只会让柏拉图学园里的一个普通成员报以礼貌的微笑。但话说回来,19世纪的黑格尔尚能呵斥“哲学意见/观点”(die philosophische Meinung)这类语词的荒唐,并希望把“哲学”这个名字从这类业余、庸俗、败坏的谈论中抢救出来,我们当代的哲学教授们却可以毫无难色地在讲堂、著作、文章里高谈他们自己及他人的“哲学意见”“哲学观点”了。如果说启蒙哲人把“科学体系”当作真理的唯一形式是一种“肆心”(ὕβρις)和迷醉,那么在现如今,启蒙哲人曾珍视过的那些名字(“科学”“体系”“理念”“理论”等),其成色已经低劣、稀薄到了一个地步,以至于那些连一本正经哲学书都没读完过的人,都在大谈着“我的理论”“我的理论体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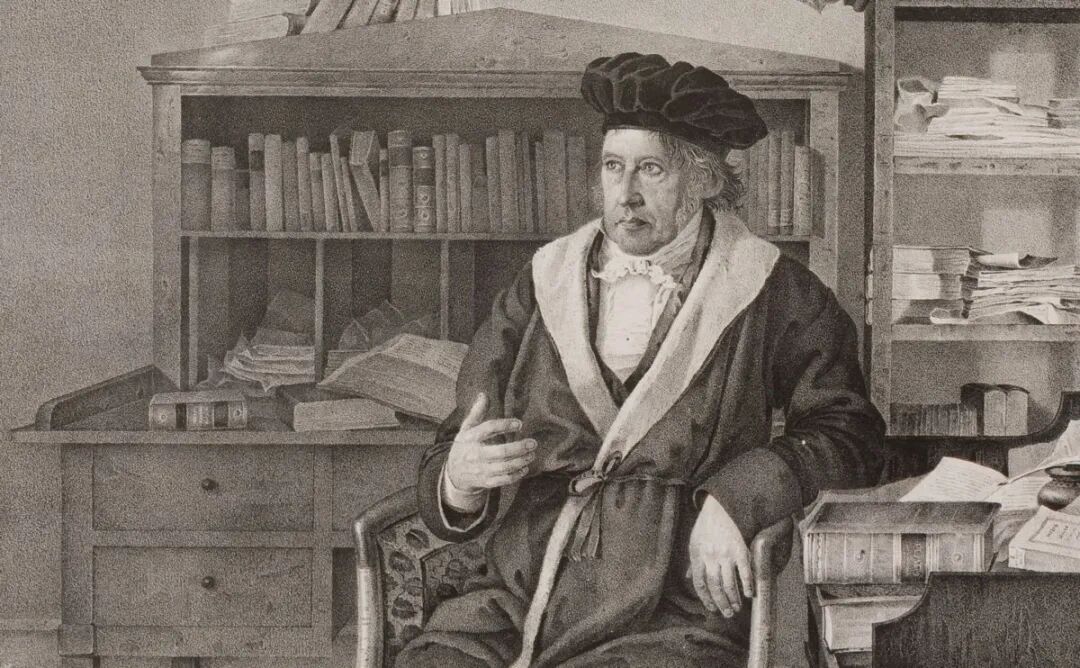
哲学、科学、理论(古典哲学语境中,三者同义)是“西方—欧洲之物”,更严格地说,是“希腊之物”。对笔者来说,了解这种特殊知识方式在古希腊语境中的诞生、本性及特征,乃是不可回避的职业义务。因为唯有如此,一个人才能从当今这种混乱的智识情势中获得一个合适的观察、诊断距离,才可能“科学地”(古典哲学意义上的“科学”)处理我自己所关心的古印度秩序现象。因此,在此后的时间,笔者一直在努力熟悉古典哲学,学习古典哲人和少数当代政治哲人对秩序现象的处理,操练从意识问题(“灵魂学”“哲学的人学”)去思考、理解个人、社会的秩序问题。
“哲学”“科学”“理论”等词以及它们所标记的那种特殊的知识方式,虽然诞生在希腊古典哲学的语境中,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它们的意义和蕴含在后世却历经流变。
在中世纪,哲学或科学被理解为“自然理性”(ratio naturalis)在“启示”带领和监督之下的理解活动,它是衬托和襄助神圣亮光的荧荧蜡爝。但在启蒙时代,它被视为“人类理性”(die menschliche Vernunft)[4]自主运作、运用的产物,成为人间唯一可靠的光源,是启蒙哲人用来驱逐“超验命题”“传统”甚至“迷信”阴影的火炬。
从引导人走“向上[的]道路”的“生活之拯救”(σωτηρία τοῦ βίου),成为神学的使女(ancilla),再从使女升高为主母(domina)乃至女王(regina),从古典时代到近现代,哲学的内容和地位一直在变化。不过,无论是倚仗“神性努斯”,还是借道“自然理性”,抑或是凭靠纯世俗化的“人类理性”,“哲学”(“科学”“理论”)所标志的知识活动在各个阶段至少拥有一个共通的东西:它是一种属理智的活动,通过理性讲述、论证、推求、论量去寻获某种普遍之物。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有当代学者忽略、越过古今知识品质差异,将西方传统中这种知识方式一律概括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
这种概括是否充分,是否过于笼统,此处不作讨论。笔者想要说明的是,在古典哲学语境中,φιλοσοφία[哲学]、ἐπιστήμη[科学]、θεωρία[理论],固然也是以logos[论证、理性]为核心,但它们并非近现代以来的那种基于世俗理性(即工具理性)和纯客体逻辑的认知活动。相反,它们总是强调以永恒存在为尺度,以期获得对万物真实秩序的一种“看见/照见”(θέα, ὄψις),并以论证(λόγος)或知识辩论(διαλεκτική)的方式传达这种“看见/照见”。

因此,根据古典哲人的构想,“哲学”“科学”“理论”固然离不开作为传达方式的“逻各斯”(论证、运算理性、逻辑、普遍性陈述),但它在人类灵魂中的经验(πάθος)基础,绝非像近代哲学那样仅对作为传达方式的“逻各斯”本身产生狂热,而是对存在——尤其是作为万物根基的永恒存在——本身的热爱(ἔρως)。虽然近现代哲学和古典哲学被不加区分地归入所谓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但两者所呈现的“生存姿态”完全不同:前者是一种自我肯定的“肆心”(表现为“未来一切……的先导”“科学体系”“决然的开端”,再堕落为各种“主义”“终结”等),它强调属人的权能;后者则是一种自我否定式的谦卑(表现为“无知之知”“自知无知”“人不是万物的尺度”等),它强调人向高于自身那个尺度的屈服。
这本小书的标题是“印度古典文明原论”。笔者冒昧以“印度文明”为主题,并非想大包大揽,而是为了拟定标题的经济。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先简单解释一下标题,并借此对此书主题和内容的范围作出限定。
首先,标题中的“印度”,严格说是Hindu[印度教的],而非意义更宽泛的Indian[印度的],因此本书实际上在讨论主体的印度教文明,不涉及同属印度雅利安文明的佛教、耆那教等传统,更不涉及南亚次大陆上的非雅利安文明。其次,标题中的“古典”不指涉古印度年代上的“古典时期”(classical period),而是在体性上标记文明的“典范阶段”(classical stage)。在“印度古典文明”这个特殊的阶段,决定和塑造后世印度文明的典范性、尺度性典籍——śruti[天启听闻]与smṛti[记忆传承]——逐渐得到成立;从实际历史角度来看,该阶段涵盖了印度历史的整个上古、古典时期。[5]
▲ 吠陀时代(公元前1500年—前500年)的
印度文明示意图
对于被外国人称作“印度教文明”(Hindu civilization)或“印度教”(Hinduism)的传统,印度人自己有两个更直接、更朴素的名称——“永恒的法”(sanātana-dharma)或“吠陀法”(vaidika-dharma)。对历代印度人来说,dharma[法]是支撑、维持宇宙、社会、个人生活正常运行的基底和原则,因此它是“永恒的”(sanātana);同时,由于dharma得到开显的媒介(dvāra, mārga)是吠陀圣典(veda)或“天启听闻”(śruti),因此它又是“吠陀的”(vaidika,源出于吠陀)。当dharma落实到人类事务当中时,它既是渗透到政治社会和个人方方面面的教化内容,又是针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整全规范。由此可知,在印度人的自我理解中,“永恒的法”“吠陀法”的内涵远比单薄的“教”“主义”或-ism更丰富,它乃是共同体和个人的生活方式(vṛtti)。
本书的核心任务,就是着眼于古印度人自身对印度教的自我理解(“永恒的法”“吠陀法”),尝试在印度雅利安(Indo-aryan)文明统绪中去探究它那个格外浓缩却丰富的内核——dharma[法]。因此本书冒昧题名为“原论”。这个“原论”不求面面俱到,也不求展开太多细节,目的仅仅是对印度教文明中的dharma作一番总体的、宏观的考察和清扫:尝试描述它在印度秩序思考中从前身、诞生到巅峰形态的历程,并在印度教文明本己的精神、智识、文化语境中去自然地呈现其阶段性形态,同时廓清其意义和蕴含。
在哲学——尤其是关于人类事务的哲学——这一心灵秩序的决定性创立者苏格拉底(Socrates)那里,哲学(科学、理论)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渴慕和追求智慧、知识)、一种生存姿态(知道自己无知)。而这种生活方式和生存姿态的内核,就是人对自身缺陷的意识(“人不是尺度”),并通过这种清醒的意识来整饬自身的生存。

职是之故,在对过往文明当中秩序思考、秩序思想进行追溯和阐释时,一个探究者不应将自身或自身所处的当下当成尺度,更不应把自己摆置在完全“客观的”阿基米德点,高高在上地俯视他的“研究对象”。相反,他首先需要入乎其内,与他所探究的先贤一道,去设身处地地寻求关于秩序——宇宙的、社会的、个人的——的知识。
哲学(科学、理论)首先是一种生存形式(渴慕和追求真实),然后才是输出和传播知识(说服他的侪辈)。因此,对于一个古典意义上的“理论人”或“科学人”来说,知识首先须是切身的、活跃在探究者自身灵魂中的知识,然后才是对象指涉的认知性知识。因此,对过往秩序现象进行考察、探究、阐释的过程,同时也是探究者唤醒、恢复其自身生存秩序的过程。哲学生存(philosophic existence)的标志,不是生产、输出关于“研究对象”的认知性、命题性知识,而是在认识“研究对象”的过程中认识自我,并认识梭伦(Solon)所说的那个“不可见的尺度”(ἀφανὲς μέτρον)。
[1]比如以下典型做法:以现当代各种——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的——专断论的“哲学”“政治学”言说方式(即各色“主义”类型的“理论”)为标准,去印度古代文献中提取各种“思想”“观念”“理论”“意见”,再进行陈列、评述、判断、讲论。
[2]正如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逻辑研究》第一卷导言中——引用穆勒(J. S. Miller)的《逻辑学体系》——所说:“不同的作者仅仅是为了表达不同的思想(Gedanken)才运用同样的语词(Worte)。”
[3]以上引文出自《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前言,强调(此处为斜体)为黑格尔本人所加。
[4]die menschliche Vernunft是康德(Immanuel Kant)《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1781)前言中开篇的词组。这并非偶然,它是“人类理性”在当时日益“自我主张”(Selbst-Behauptung)趋势在智识领域的表达。
[5]印度历史上的“上古时期”指孔雀帝国建立之前;“古典时期”指孔雀帝国建立至笈多帝国灭亡(参看本书第三章引言及注释)。另,“天启听闻”指整个吠陀启示文献;“记忆传承”主要指吠陀支、史诗、法论文献(这两个名词,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朱成明,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印度古代政治秩序、印度哲学、印度西方比较哲学。